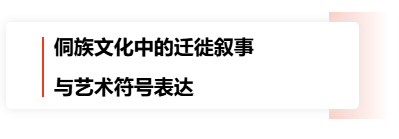
(1.贵州民族大学美术学院,贵州·贵阳550025;2.贵州财经大学艺术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作者]:张琰,贵州民族大学美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民族历史文化、视觉传达设计;徐波,贵州财经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传统村落建筑设计、少数民族传统文化。

(徐波)

(张琰)
[摘要]:在流传于贵州、湖南等地的侗族文学文本中,存在鲜明的祖宗迁徙叙事。文章讨论这些迁徙叙事的叙事结构以及导致迁徙的多重原因,基于此探讨侗族文学文本中所体现出的自我建构、他者阐释与身份区隔,最后结合迁徙叙事与身份建构对侗族集聚区常见的铜鼓等符号进行讨论。
[关键词]:侗族;迁徙;符号表达;身份;艺术
侗族主要分布在黔、湘、桂交界处。《祖宗上大河》等反映先民迁徙的文本是侗族文献之中较为常见的文本,许多侗族人传唱的古歌中都有相关反映迁徙的内容。目前,学术界关于此类文本的研究还有较大推进空间。文章基于湖南、贵州等地侗族文献中描写迁徙的文本,对侗族视域下的迁徙叙事结构、迁徙原因、迁徙目的、族际关系以及身份表达进行探析,并基于此讨论侗族主要符号的来源和发展,旨在从侗族人的视角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对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2024年贵州·从江第十七届侗族大歌节侗族大歌歌唱大赛现场)
图片来源:贵州民族报社
一、侗族古歌中的迁徙叙事
西迁是侗族祖源叙事中的主题。祖源歌是侗族古歌中的重要文本,侗族人在婚丧嫁娶和重要节庆等活动中,一般会请能说会唱之人吟唱祖源歌。各地侗族祖源歌主要叙述先民的来源和迁徙过程,其中关于迁徙路线的描述不尽相同,贵州大多数侗族古歌都提到自己祖先是居住在中国南方的古越王后代,这也得到一些学术研究的证实。学者考证认为侗族是“干越”的遗裔,“干”即鸟巢、巢居之意[1]。综合各地文献看,侗族祖先主要从福建、广东、广西、江西等地自东向西迁徙,途中经历多次中转和经停,重要经停地中就有吉安、梧州等地,后又因遭遇洪水、灾荒、兵燹等原因造船继续西迁,最终沿河而上在贵州、湖南等地寻得土地肥沃、地势平坦的理想居所。这是常见的侗族祖先迁徙叙事。这种迁徙叙事遵循着多次寻找空间意象的叙事模式[2]。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研究表明这种迁徙叙事并非纯粹的文学臆造,而是具有一定历史真实性的史料,学者根据侗族古歌中常见的梧州、燕州、浔州三个地名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考证出侗族人开始从广西向贵州等地迁徙的时间在唐代前后。因此,不能简单将反映迁徙内容的侗族文献视为民间文学作品,对这些承载着侗族人历史记忆的文献应给予更多关注。
黔东南等地侗族文本大多将自身祖先追溯到福建、广东等东部地区。榕江三宝侗寨萨玛祠中,有一口1838年的《名垂万古》碑,据碑文,侗族始祖由浙右之粤,移徙雷州星县,沿河而上,寄迹于斯。这一时期,尚有十二姓从东部迁徙而来的历史记忆,但对迁徙至此的时间并没有准确的记载,仅有“越元明清”一语。在20世纪编辑的黔东南的《侗族古歌》中,这种迁徙叙事仍旧存在,古歌称侗家祖先原住福建,后逃荒至江西吉安府朱子巷,在惹出祸端后才迁往梧州,在梧州因为种田无收迁往柳江[3]。在西迁过程中,梧州是一个重要中转地,当然也有一些古歌称自己的祖先直接从梧州开始迁徙。20世纪80年代,杨国仁等学者在黔东南采集的20首古歌中就有11首提到侗族祖先从梧州迁至贵州。榕江等地古歌也提起侗族祖先从梧州郡县、浔州河畔迁出一事。据《侗族祖先》载:“当初侗族祖宗,不在别处,在那闪烁的梧州,从那浔州来。”[4]然而梧州并非侗族人的最终定居地,侗人逃至梧州后遭遇洪水,又乘船继续逃亡。黎平县的《祖宗上大河》称侗族人曾沿珠江上至柳州,湖南衡州的侗族古籍中则称其祖先是从江西府太和县迁至衡州。
侗族先民迁徙的原因既有天灾亦有人祸。就天灾而言,干旱缺水,粮食歉收,土地贫瘠,洪水暴发都是常见的原因。在自然因素中,地力衰竭、取水不便等是导致迁徙的重要原因。从江地区的《查公卜》中就称人们迁徙乃是因为种地不出棉,耕田不出粮,养不了人,吃不饱饭,奔逃迁徙。此类叙事不仅见于从江县的文献,还见于其他地区的侗族古籍之中。
人祸之中,官府征粮和持续的兵燹是常见的原因。例如榕江地区的古歌中就提到官府攻破古州,总督攻打侗族居住地,其时炮大如庞桶,枪粗如禾晾竿。战乱诱发劫掠,人们搜银搜粮归长官,搜米搜麻归属下,侗族人因此穿上草鞋开始迁徙。衡州侗族古籍也称,其祖先迁徙的原因是昼派粮、夜捐米,忍吃也难完税,只好迁徙。这些迁徙的侗族人最终想追寻的是一个土地肥沃、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居所。此外,风俗习惯不一也是侗族祖先迁徙的原因。衡州侗族文献就提到,侗族人曾因为“喜酒吃双餐,礼仪难酬还,只好把家搬”,也曾因互相嫉妒而“气难忍,诽议难当,只好迁他乡”[5]。当然,侗族人之间还会出现自我分化。
侗族迁徙的目的是寻找便于耕作的小流域平地。湖南、贵州等地侗族古歌都曾提到,祖先不断迁徙是为寻找可供耕作的平地。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的《宗支簿》中就有因为田在高处,水在下边,脚不会踩水车,手不知做水车,只好又搬迁这一记载。1960年在从江采集的侗族古歌《查公卜》中也有侗族人从前不会造水车和龙骨车的相关记载。质言之,导致迁徙的一个原因是居住地地势过高,侗人又不会造水车,因而引水不便,田高水低就导致种地不出棉,种田谷歉收。关于侗族祖先找寻平地,还可从榕江地区的《三宝根源歌》中得到证实,侗族祖先从梧州迁到三宝田坝“大海子”,在此开荒种田种棉花,因地势平坦、水源充足,土地肥厚稻禾穗长棉大朵,池塘鱼肥有腿大。可见,寻找平坦的土地是为了获得丰收。根据侗族自称Kam一词词源,也可印证侗族祖先迁徙是为了寻找平地、平原地带、濒河可耕的平地或是山间盆地。
综上所述,在侗族祖先叙事体系内,流动性是主要特征。促使侗族流动迁徙的原因中,有地力耗尽、作物产出降低、洪水暴发,人们难以维生的现实原因,但很难就此认为这些原因是促使他们迁徙的主要原因。质言之,这种迁徙并不是被动的,更多是主动的,是侗人为了躲避战争,保持自身特色,追求安定、富足生活作出的主动选择。这种迁徙也是为了防范因内部分歧而导致的混乱和冲突,从这个意义上看,迁徙也是一种保持单一性、独特性的有效方式。

(从江县侗族群众盛装出席侗族大歌节活动)
图片来源:贵州民族报社
二、侗族视域下的他者与自我
对周边未知区域的人进行污名化或浪漫化是一种常见的历史现象,但侗族人并未形成这种叙事体系。欧洲人在对外扩张过程中就形成了几种固有的他者想象和阐释模式,[6]这些叙事中都存在一个特定的叙事中心,生活在中心的人以自己长期定居的区域为地理上和阐释上的中心,将中心之外的他者视为应被驯化的蛮夷和化外之民。这一叙事也是奠定欧洲中心主义和殖民活动的基石。然而,在侗族文化中,这种通过浪漫化或污名化他者来界定自我的做法并未盛行起来。
在侗族人看来,侗族与汉族、苗族等为同根同源的骨肉关系,这主要体现在其创世神话中。侗族人认为自然中存在的山川湖泊、花鸟虫鱼,甚至是风雨雷电皆有灵,诸灵之间又有相同的源头,人与人、族与族更是同源[7]。根据贵州侗族文献,开天辟地后,四个龟婆孵出松桑和松恩,松桑和松恩生下12个孩子,其中只有章良和章妹为人,余者是鸡、鸭、虎、熊、雷婆等禽兽怪物。章良和章妹放火烧山后人兽分开、雷婆上天,雷婆逃上天后降雨酿成大洪水,章良和章妹躲在葫芦里逃生。此后章良和章妹结为夫妻生下怪子,他们将怪子剁为碎块扔遍全山,次日一早漫山碎块化为侗、汉、苗等各族人,其中肉成侗族、肠为汉族、骨为苗族……榕江地区的古歌也有肉化成侗族,肠化成汉族,骨化成苗族的记载,是为人类起源。相似传说还流传于湖南侗族间,不同的是他们认为姜良、姜妹兄妹结亲后所生怪物被斩碎后,指化为峰、骨化作岩,肝肠落成长江大河,这些要素构建起364姓人所居的世界,其中瑶人祖先坐八面山坡,依靠自然过活;汉人祖先坐天下,衣食无忧;侗人祖先养鱼种稻,逍遥快乐。可见侗族与汉族等民族的差异在于生活方式、生活环境不同,但他们的起源都相同。侗族与周边壮族、傣族等民族间的同源关系也得到学者研究证实。据考,侗族、壮族、傣族同源,且在秦汉之前开始分化[8]。
侗人认为“我”与“他”的不同主要在于语言与习俗的差异。侗族人在迁徙过程中会与其他民族产生交流,但很少与其他民族杂居,例如1960年在从江地区搜集的侗族古歌之中就有:汉人住水边,侗家住平处,苗家住高坡;以及苗族吃上方田,汉族吃下方田,田丘由汉官收,人们由官府管这一类关于民族关系的描写。在此类记载之中,侗族与其他民族各居一方,同处于官府治下,彼此间保持交往交流。但在与他者的对比和交流中,侗族人也逐步意识到自身与苗族衣着各样,且话不相合,言不相通。我亦我,他亦他。此处区分身份的主要是语言、习俗和服饰。侗族人并未形成自己的文字,而是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自身历史文化。贵州、湖南等地侗族文献中,都有侗族靠口头传颂古典,其他民族用文字传承文化的描述,即汉人有书记古典,侗家无文靠口传。祭祖,靠嘴。在侗族人口传的文本中,大歌、祭文等是主要内容。据学者考证,侗族大歌一般有专门的歌班传承,流传开来的时间迄今已有500余年[9]。
侗族人追求和平、爱好音乐,但在侗族语境中,躲避战争、崇尚音乐并非古已有之、生而有之,而是经历过一次历史性转变。据贵州、湖南等地侗族大歌记载,在三国时期,侗族人曾准备与官府抵抗,但最终被多谋善计的孔明巧妙化解,孔明设计使人们的关注点从武力抗争转移到斗牛和对歌作乐上。易言之,侗族人经历过一个从武力抗争转向主动躲避战争、崇尚音乐的历史过程。明代学者邝露也曾对侗族的这一特征进行过生动的描写,称侗族人也是僚类,不喜杀,善音乐。弹胡琴、吹六管、长歌闭目,顿首摇足,为混沌舞。这表明明代的侗族人还被纳入化外之人讨论,但作者也记录了他们的两个重要特征,即不喜好战争,且善于演奏管、琴等乐器。侗族人不喜厮杀的特征一直延续后世,以致榕江的古歌中还有别人祖宗知守地,咱祖宗只知逃奔这一说法。可见,无论是他者视角下还是自我认知中,热爱和平和喜好音乐都成为侗族的独有特征。
在侗族迁徙过程中,其他民族对侗族的认知和界定并不是统一的。侗族新迁入一个区域时,当地居民往往会按照固有的认知体系,赋予侗族人一个新身份,这种身份的赋予并非完全基于他们对侗族的了解,反而时常受他们与周边既有民族关系的影响。衡州的侗族人就称先辈在迁徙中被上边来的称汉人,被下边来的又称苗家。外部人看,侗族与汉族、苗族别无二致。这种由他者给定的身份作用于侗族之后,一方面刺激部分侗族人继续迁徙,另一方面也促使他们发现自身与周边汉族人、苗族人等的相似处,因此实现交融。事实上,侗族与周边民族在文化上也是共享的。侗族古歌中出现的唐王、孔明、龙王、雷公等都是各族共享的文化符号和历史记忆,而非侗族所独有的。

(黎平县肇兴侗寨小朋友身着节日盛装参加侗年巡游活动)
图片来源:贵州民族报社
三、群体观念与符号表达
在侗族艺术符号系统中,与承载群体意识的鼓楼、铜鼓、风雨桥相关的艺术符号更为常见、更加主要。这些主题的符号时常被设计、重组后运用在民族形象展示、商业宣传等各类场合,并日益成为侗族的主要象征。为充分挖掘此类符号的潜力,有必要对这些主要艺术符号及其元素的生成语境和历史文化底蕴进行剖析,进而创造出更多接续传统且契合新时代的视觉符号,传达侗族人流动中的风情与神韵。
侗族文化中有鲜明的群体观念和共享意识。古歌中特别提及在分食鱼肉等食物均分给八方众人,提倡获得食物的个体不应独享藏私,而是要散给众人同享共乐。古歌中还有专门内容指出独吃食物会额肿,齐吃则会快长,分而食之的习俗反映的是侗族人所秉持的集体观念。一些侗族古歌还将读书入世与串寨游乡村相提并论,并凸显集体生活的重要性。这种集体观念也反映在侗族谚语中,例如“一人住,成不了村寨;一人走,踩不出路来”等。一言以蔽之,集体观念和共享意识在不断被强调和凸显,可以说形成了一种维护村寨集体利益的“村寨意识”[10]。这种集体观念影响着侗族人的符号生成、选择和身份表达。
鼓楼和风雨桥是侗族人的主要聚集空间,群体观念在此得以不断再现和更新。侗族村寨一般选在山环水绕之地,侗寨中心地带“龙穴”处设鼓楼,鼓楼集塔、楼、亭为一体,外观多呈杉树状,楼中置鼓,楼体布有各式题材的雕塑[11],需召集人们议事时则登楼击鼓,各寨闻鼓声后齐聚鼓楼之下。除存鼓外,鼓楼还有祭祀、预警、休闲娱乐等功能。例如侗族人在祭祀神祇时就会在鼓楼前聚集,进行宴饮、踩歌和举行仪式[12]。鼓楼前一般有一个广场,作为聚众议事、对外交流、文化展演等活动的主要场所。鼓楼作为侗族符号载体,承载着神话传说、祖源观和信仰等文化底色,但在鼓楼楼体雕塑中,也有桃园结义故事、文昌君、土地爷等相关主题人物,这本身就体现着多民族文化融合[13]。另一具有侗族特色的建筑是风雨桥。侗族风雨桥集桥、廊、亭为一体,既是遮风避雨、连通两岸的交通要道,也是聚集人群、展示文化的公共空间,风雨桥上一般设有供人们祭拜的神龛,桥体、桥顶、桥脊上常雕有各类飞禽走兽。
从发生学角度看,一般视作侗族特有符号的铜鼓,在起源上是多元文化交融的产物。据蒋廷瑜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前,侗苗错居的地区使用铜鼓的习俗较浓,这些区域保存的铜鼓也较多,但进入21世纪以来铜鼓的使用频率开始降低。铜鼓虽是侗族代表性符号和常见乐器,许多侗族村寨中往往都会设楼置鼓,但铜鼓并非侗族特有,而是常见于中国南方少数民族聚居区。壮族、苗族、瑶族、布依族、水族、彝族都有关于铜鼓的口头传说。在这些传说之中,铜鼓往往都是外赠的,赠铜鼓者主要有龙、孔明。在侗族关于铜鼓起源的传说之中,铜鼓也是源自孔明的赠予。相传三国乱世,侗族人逃入深山后无以为乐,孔明造铜鼓教人作乐,是为孔明鼓。无论是孔明鼓还是龙赠鼓,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象和历史相联系。
常见于侗族集聚区的许多符号在来源和意义生成的路径上都不是单一性的。在风雨桥和鼓楼顶部,一般会有葫芦形装饰。葫芦在侗族创世神话中别有深意,章良和章妹就曾躲在葫芦中得以躲过大洪水,但侗族人在使用葫芦符号时,也借鉴了阴阳说,主要体现为葫芦装饰物的节数一般为代表阳性的奇数,为吉祥之意。此外,这一符号还与道教中铁拐李的葫芦兵器以及“福禄”谐音不无关系。在侗族建筑、雕塑和织物等中,龙、鱼、杉树都是常见符号,但这些符号并不是侗族人所独有的。据研究,黔东南侗族在服饰上借用了苗族等民族的花纹配饰等元素,同时这一地区的苗族和侗族在环形银项圈、银手镯的样式上也存在互相借鉴的现象,在具有民族特色的刺绣和饰品中,鱼和凤凰的图案是普遍文化符号[14]。
总之,从符号生成视角探讨侗族文化中的鼓楼、铜鼓、风雨桥等符号的意义生成路径发现,迁徙是侗族祖源叙事中的核心词汇,以村寨为认同对象的集体观念在迁徙过程中不断受到强化,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侗族文化具有封闭性。相反,侗族不仅在迁徙中实现了地理位置上的流动,还在与周边苗族、汉族等民族的交往交流中实现了文化交融。开放性和融合性是侗族文化符号生成过程中的基本底色,也应成为未来侗族文化符号发展的方向。

(侗族对歌)图片来源:贵州民族报社
四、结语
在侗族祖源叙事中,迁徙是一个常见的词汇。关于迁出地的描述很多,闽、粤、桂等地在侗族古歌中都有提及,其中梧州等地更是重点被提及。关于迁徙原因的描述中,地力耗尽、自然灾害、兵燹之厄、苛捐杂税、风俗各异皆有。侗人在迁徙和流动过程中并没有生成污名化他者的话语,而是将自身与周边民族视为同根同源不同俗的关系,在其他民族看来,侗族与周边居民也别无二致。从文化符号看,常见于侗族集聚区的鼓楼、铜鼓、鱼图腾、凤凰图腾等文化和艺术符号都是民族交融的产物。侗族文化在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催生,也应在新的交往交流交融中重新焕发生机。
参考文献:
[1]张民.探侗族自称的来源和内涵[J].贵州民族研究,1995,(1):90.
[2]芦静静.侗族迁徙古歌中的空间意象研究[J].民族艺林,2019,(4):90.
[3]杨国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间文学资料(从江侗族民歌专集):第一集[Z].内部资料,1985:175.
[4]张民,普虹,卜谦.侗族古歌[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1:41.
[5]湖南省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中国少数民族古籍侗族古籍之一:侗款[M].长沙:岳麓书社,1988:299.
[6]王晓德.古典传统与欧洲人对美洲的早期认知[J].世界历史,2023,(3):55.
[7]索晓霞,肖立斌.贵州少数民族的语言哲学[J].贵州民族研究,2024,(6):147.
[8]范宏贵.侗族祖先迁徙地点、时间及其他[J].广西民族研究,1989,(4):67.
[9]杨毅,冯慧敏.侗族大歌传承的意义及范式研究——以黎平县侗族大歌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24,(3):115.
[10]谭志满,杜鹏.侗族民间信仰中的“村寨意识”探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5,(11):117.
[11]秦越,李云云,马小成.从符号编码看侗族鼓楼的文化渊源及当代价值[J].贵州民族研究,2022,(6):134.
[12]赵宇翔,张荣军.西南少数民族节庆仪式中的血祭及其人类学解读[J].贵州民族研究,2022,(6):147.
[13]蒋卫平.侗族风雨桥装饰艺术探析[J].贵州民族研究,2017,(12):139.
[14]龙寸英,李德宽.民族文化交流交融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研究——以黔东南服饰文化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22,(5):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