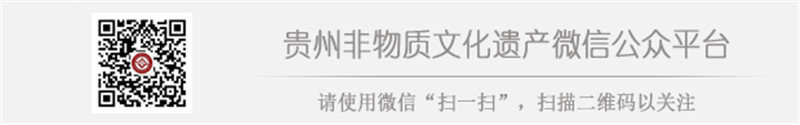【摘要】在地理学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可被视为从“空间”到“地方”的生成过程。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于地方具有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等多重赋能价值。在赋能地方发展的过程中,需要谨防因“博物馆化”“过度商业化”和“过度旅游开发”而陷入“无地方”与“非地方”的困境。对此,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开拓保护与发展“双赢”新路径,面向“六位一体”的城市目标体系彰显担当,深化对地方的涵育功能,推动与时俱进的时代审美和价值阐释,充分发挥非遗数字基座在赋能中的基础作用,赋权多元非遗主体,运用新科技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阐释传播工作,以文化生态保护区为依托深化整体性保护,处理好全球与地方的关系,讲好“中国故事”,实现非遗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赋能。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文经济;地方;文化赋能;可持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绵延传承的活态载体,也是文化多样性的鲜活样本。2022年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①。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发展好我国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对于赓续中华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对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赋能价值。
2005年8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中指出:“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将文化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凸显了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③。2025年3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期间,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深化城乡精神文明建设,优化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④。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亟待厘清的核心关系⑤。
对此,本文旨在从地理学视角出发,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机制,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于地方的赋能意义,辨析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赋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大忧思,并给出可持续赋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径建议。
一、从空间到地方:
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能的地理学思考
在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中“民间创作”的概念基础上,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并发展出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非遗公约》)这一国际法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基础。由于翻译的原因,最为广泛流传的《非遗公约》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⑥。这里“场所”(Forum)和“空间”(Space)出现混译的情况,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⑦,进一步强化了“场所”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化空间”价值被淡化。
对此,向云驹认为,文化空间的概念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是一个具有启示性的指称,它是一种理念,是一种文化形式或类别,也是一种保护实践。文化空间为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科学的范式和全新的视角,对尚未使用文化空间概念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传承、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应该引起进一步的研究与讨论⑧。
相较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以及民族学、文化学等学科对于文化空间的探讨,地理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文化空间”的关注呈现两种倾向:一是认为文化空间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容器”,即狭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掘、保护、阐释、传承的场所。二是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的特征和影响的地理因素,如程乾等利用GIS空间分析,得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呈带状、组团状,分布在东部(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相对稀少等……宏观尺度分布受地理大环境影响,其分布受物产和人类活动影响较大”的结论⑨,类似的研究从不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分布,再到不同类型的非物质文化空间分布的研究可谓众多,但皆未充分发掘文化空间的丰富意涵。
文化空间,不仅是一个具有相对明确边界和独特环境的村落、海岛、广场等空间,而且具有独立的民族群体、社区以及独特的语言和历史,更重要的是生活于社区中的群体与文化空间的互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上对“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问题的回应,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的、当代且活态的、包容的、代表性的、基于社区的”诸多特征,这些特征皆强调人与人的互动、分享、传承及人与社区的互动关系⑩。
当然,若按照上述对文化空间的理解,文化空间应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应有之义,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地理学意义,在于其不能被简单的“对象化”,而是需要更为深入的历时性思考。正如朱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空间》一文中审视了“文化空间”概念的裂变,提出需要“以物质为对观(非对立)解非物质之精髓,以无形化有形综传统之大观从‘对观’(比较)的方法论层面强调了文化空间的重要价值”⑪。对此,本文在此基础上引入“地方”的概念,探究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地理学机理。
地方作为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其源流深受印象学影响,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使用栖居(Dwelling)一词描述人与地方的互动方式,并将人与地方的联系上升至哲学存在方式进行讨论⑫。20世纪70年代后,以段义孚(Tuan Yifu)、爱德华·雷尔夫(Edward Relph)等为代表的研究者将这一概念引入人文地理学科的研究中。段义孚在其经典著作《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专门介绍了空间与地方的转换机制,即“空间被赋予文化意义的过程就是空间变为地方的过程”⑬。当前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冲击不仅深刻影响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也加剧了“空间—地方”的紧张关系⑭。从这个意义来看,有别于其他学科的思考,地理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解,可以视为将“空间生产”转变为“地方意义生成”的过程。这个赋能过程的前提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深深扎根于地方的传统文化历史中,倘若不顾于此来谈“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等于从根上肢解了它的有机生命,摈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为根本的活态特征,文化也就不再是活的文化⑮。所谓抢救和保护,也就会徒具形式,更遑论利用和赋能。
从地理学尺度上看,物质文化遗产强调“突出的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要求在对应尺度上凸显其不同的普遍价值。《非遗法》第三条界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体内在价值,即“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⑯;第四条彰显其外在价值,即“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注重其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⑰。并且,在第十八条中,使用“重大”这一程度词,进行国家级与省、自治区、直辖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区分,要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大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省、自治区、直辖市级在“本行政区域内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尺度差异。
较之于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形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强调“无形性”,具有“润物细无声”的传承价值。我们常听说的“非遗即生活”正是这种价值的形象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溢出价值要更为彰显。非物质文化遗产能为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不是简单的直接相关关系,而是表现为一种精神动力,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区域的内部聚合,即将区域内部人们的积极特性聚合起来,从而为特定区域的经济发展提供可持续动力⑱。对此,有学者较为全面地总结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辐射效应,具体而言是打造了地方名片,促进当地旅游及相关产业发展,促进当代社会环境和谐,发扬了民俗文化,促进临近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⑲。
2024年2月1日至2日,习近平总书记赴天津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他提到“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以下简称“四个‘以文’”)。四个“以文”作为内涵丰富、思想深邃、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为我们更系统性地指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路径,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重要意义⑳。在“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示精神指引下,对照四个“以文”,将“文化”嵌入“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活态场域,强化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指向,更有了可持续的生命力。
(一)以文化人,在口传身授中铸魂育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不只在文化表现形式本身,还在于代代传承的知识和技能。这种知识传承的社会和经济价值意义重大,无论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同样重要㉑。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技艺的呈现,更是价值的代际流动。苗绣的一针一线、昆曲的一腔一调、二十四节气的一叶一花,都承载着“敬天惜物”“和合共生”的东方精神。让非遗进校园、社区、网络课堂,让老匠人成为“活教材”,把技艺流程变成“思政脚本”,把乡土故事转化为“德育案例”,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代际传承中实现教化功能。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活态性、民间性和生活性特征,它的保护就不只是哪一个时段、哪一个部门、哪一部分人的事,而是一个全社会经常性的事,尤其是一代又一代后来人的事,让“保护”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代代相继,进而实现以文化人,铸魂育人㉒。正如弗里曼·蒂尔登(Freeman Tilden)所言,“对祖先留下的遗产怀有一份深远的觉知,是我们面对未来不可或缺的精神要素,借由将过去保持成一个生机盎然的实体则可帮助我们获得此觉知,这正是一种力量”㉓。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潜能,正是通过其自身的整体性(Wholeness),促进人的整全性(Wholesomenss)㉔。
(二)以文惠民,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小手艺”可以促就业,撬动“大民生”,让人民群众的增收获得就地满足。2022年4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五指山市水满乡毛纳村考察,察看了黎锦技艺、黎族藤竹编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强调要搞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全面振兴有效衔接㉕。类似毛纳村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政府搭台、传承人唱戏、群众得实惠。通过成立非遗合作社,盘活竹编、草柳编、土陶等各类非遗工坊,就能让留守妇女“背着娃、绣着花、挣着钱”。非遗研学、非遗夜市、非遗康养等新业态,把“指尖技艺”转化为“指尖经济”,实现地方百姓增收,从而达到真正的惠民效果。同时,在“人民创造文化”与“文化滋养人民”的辩证关系中,文化供给质量直接关乎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㉖。在公共文化空间中植入皮影戏夜校、木版年画DIY、中医义诊……能为人民群众打造更多颜值高、内容多、服务新的“文化客厅”,从而更好地保障人民的文化权益,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
(三)以文润城,促进历史文脉与现代生活共荣共生
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地方文化基因融入城乡协调发展的毛细血管,使得街巷有故事、转角遇匠心。2025年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黎平县肇兴侗寨,观看侗族大歌表演,察看村寨风貌和侗族文化展示中心,深入侗乡织、染、绣特色产业基地,同乡亲们亲切交流,指出古朴气韵离不开妥善保护,时尚气息得益于活态传承㉗。漫步苏州古城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苏绣、宋锦、缂丝、苏扇等非遗匠心独具,游客可在此沉浸式体验“食四时之鲜、居园林之秀、听昆曲之雅、用苏工之美”的“苏式生活”㉘。一条中山路,千年泉州史,中山路上南音弹唱、提线木偶、变脸、蟳埔女簪花围等非遗事项散发着古城特有的魅力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让地方历史记忆与人间烟火交汇融合,城乡文脉和现代生活共荣共生。
(四)以文兴业,利用“非遗+”跨界融合激活地方经济活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文化产业开发,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获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非遗法》第三十七条提及“国家鼓励和支持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优势,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㉚。对于传统美术和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一般通过生产性保护的方式增加项目实践频次、壮大传承队伍、激发地方创新创造活力。2011年10月和2014年5月,文化部公布了两批100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2024年,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文件认定99家企业和单位为“2023—2025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均对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的赋能示范作用。“非遗+旅游”是当前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途径,也是地方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之一。随着新技术的迅猛发展,“非遗+科技”构筑新质生产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插上了数字技术的翅膀,被开发成数字藏品,构成了可衍生开发的数字版权,并通过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转化为可体验的落地场景项目。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兴起的新型文化业态和消费模式,促进地方文旅商贸深度融合,最终实现文化繁荣与产业振兴的同频共振。
2008年,在《非遗公约》即将把90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整体并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际,缔约国大会第二届会议主席谢里夫·卡兹纳达尔(Cherif Khaznadar)就在委员会第三届会议的开幕致辞上警示了“博物馆化”“过度旅游开发”以及其他的“商业活动”三种类型的“病毒”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代表作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赋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同样面临着博物馆化、过度商业化与旅游过度开发正把植根于特定地方生活情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向“非地方”(Non-place)㉜与“无地方”(Placelessness)㉝的困境。
首先,博物馆化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其原生的社区时空中剥离,以玻璃展柜或超地方的声光电形式供游客“凝视”,使原本与仪式、节气、生计紧密交织的活态文化被压缩为可移动、可复制、可随时替换的符号商品。在这一过程中,这些用来呈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馆被弱化为纯粹的“可达性”节点,观众与展项之间仅存短暂而功能性的参观相遇,而非基于共享价值与信仰的情感联结。其次,过度商业化在一定程度上剥离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性:传统节庆被简化为按时收费的商业演出,手工艺品被批量仿制并贴上统一标签,文化空间被简单地在异地实景还原并集中展示。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传达不再回应社区内部的意义需求,而是迎合外来消费者的消费旨趣时,便失去其本应有的独特历史与文化深度,呈现出雷尔夫所言的“无地方性”——千篇一律的景观、标准化的服务流程以及面向“他者”而非“我者”的消费逻辑,进而导致地方消弭㉞。最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过度开发亦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千篇一律的古城、古镇、古街割裂了原有生活肌理,原有居民迁出,非遗传承人成为纯表演者,地方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有机联系被切断,地方沦为游客临时性的“路过空间”㉟,既无历史纵深,也难以生成身份认同。
当地方脱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前提,一味追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度利用与赋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纯粹的商业资源而非文化根脉,它所依附的地方便在博物馆化、过度商业化与旅游过度开发的三重挤压下,滑向既“非地方”又“无地方”的虚空㊱。科恩(Cohen)关于“可协商的原真性”㊲的论述提醒我们,原真性并非静止的客体属性,而是一种在社会互动中不断被再定义、再生产的意义过程。地方既未天真地要求回到“最初的样子”,也未盲目拥抱商品化,而是希望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得到可持续的阐释与传承。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深刻认知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非遗馆”“文创”“旅游”等方式来赋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并不意味着“非地方”与“无地方”的局面,更不能一味地以此为由贬损非遗的赋能价值。其关键问题不在于可不可以赋能,而在于如何赋能,在于对开发程度和阐释利用方式的准确把握。商品化亦可成为孵化器,老戏台上的灯光与音响虽非历史原物,却可能因契合当下审美的演绎,激活青少年群体的认同,进而衍生出新的文化价值。当我们邀请传承群体参与演绎,将地方性知识植入体验场景,原本虚空的“非地方”便可能转化为“再地方化”的实验场。在非遗赋能地方的过程中,地方性知识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这依赖于地方人士及其组织的力量,运用地方性知识,并最终实现在旅游及其他商业化情境下的再生产,从而实现“在了解中保护、在认同中开发”㊳。
我们用于抵御变化的方式之一是变化本身㊴。2024年3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常德河街,观看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指出常德是有文化传承的地方,这里的丝弦高腔、号子等要以适当载体传承好利用好,与时俱进发展好㊵。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正确处理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㊶。要始终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从而不断开拓保护与发展“双赢”的新路子。
第一,面向“六位一体”的城市目标体系彰显非遗担当。2025年最新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首次将城市目标体系从“三位一体”(宜居、韧性、智慧)升级到“六位一体”(新增创新、美丽、文明),体现城市发展从功能性向人本性、文化性、创新性、可持续性的全面升级㊷。“文明城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其对地方的赋能提出了更高要求。随着城市与乡村共荣的秀美图景铺陈开来,依托非遗润城润乡将更具有迫切的现实价值。
第二,深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地方的涵育功能。一是以技艺养德,让参与人通过各类传统手工艺体验,在规矩的工序里习得专注、诚信与匠心。二是以审美立品,让青年在传统文化中体认“中国味道”,完成精神返乡。三是以价值铸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中实践“见人见物见生活”,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第三,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时俱进的审美和阐释。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与时俱进,以贴近和充实人民生活为中心,提升新一代受众,尤其是年轻人的行为意愿。非遗工作者在汲取地方传统的基础上,应适当地融入新时代元素,引发当代年轻人的共鸣,从而强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认同。
第四,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基座在赋能中的资源功能。结合新一轮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新建或者更新现有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并通过引入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系统化梳理与高效调用,激活非遗资源的当代价值。通过非遗的数智化提升,当地方企业需要非遗元素赋能时,能便捷获取精准的非遗素材,从而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培育经济新增长点,让非遗从保护对象转化为地方发展的鲜活内生动力㊸。
第五,赋权多元主体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能主动性。在充分保障传承主体权益的前提下,探索以社区为单元实现非遗共管,让名录项目从国家、资本、学界的三角话语中“下沉”,由代表性传承人、乡贤、青年创客等多元传承群体共同参与制定保护利用细则㊹。
第六,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阐释传播工作。坚持活态保护优先,强调非遗回归日常生活,支持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进社区、进校园、进课堂,开展教育研学。充分利用数智、交互等手段为非遗的可见度升级提档,增强视听等体验效果,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第七,以各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为依托深化整体性保护。促进各地争创各级文化生态保护区,通过生态保护区建设维系非遗与其生存环境的共生关系,形成“保护—传承—活化”的良性循环。整体性保护不仅聚焦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本身,更注重守护其依存的自然生态、社区氛围和传承体系。依托整体性保护,形成文化“品牌”效应,提升地方辨识度,吸引外部投资和人才,使得非遗的地方价值得到持续释放,最终实现文化保护传承与经济发展的互促共进。
第八,处理好全球—地方关系,讲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国故事”。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向世界,促进文化交流与互鉴。重视民间外交,通过海外传播讲好中国地方故事,向世界呈现中国非遗的多样性,将地方的非遗魅力转化为出海的综合效益,实现赋能地方,也助力世界“读懂中国”。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专项“社会资本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4VWB01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作者简介: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文化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地理、文化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