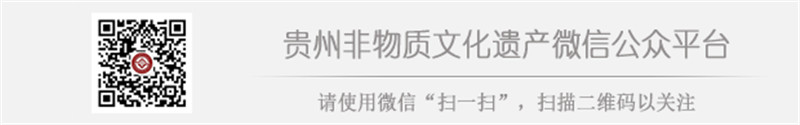主编推介

本期新青年赵尔文达,苗族,1991年生,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现就职于中共贵州省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研究方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国少数民族史等。本文指出,思南花灯的持续性展演及其蕴含的文化基因交融成为地方社会文化的生机之力,在呈现地域文化生态和构建民众生活景观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
文化生态、生活景观与地方生机:
基于思南花灯的经验分析
赵尔文达
原文刊载于
《非遗传承研究》2025年第1期。
摘 要
地方文化的产生、延续与特定的文化生态息息相关。随着地方文化的持续性实践,地方生机以一种复合联结的方式得以展现,并与文化生态和生活景观形成有效联通。“江河蜿蜒”“山川纵横”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及地方语言和信仰体系等历史人文条件,共同构成思南花灯的文化生态,并成为花灯创作与表演的文化资源。在文化实践过程中,人与花灯同构的生活景观展现在不同时序、多种场景、多样唱词以及多元形式等方面。思南花灯的持续性展演及其蕴含的文化基因交融成为地方社会文化的生机之力,在呈现地域文化生态和构建民众生活景观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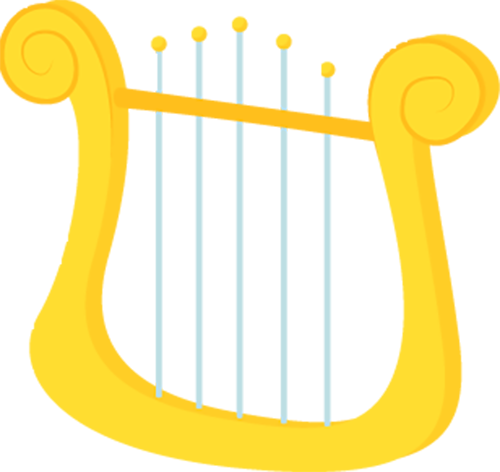
关键词
思南花灯;文化生态;
生活景观;地方生机
前 言
人及其文化与地方社会之间存在何种关联是社会学、人文地理学等诸学科所关注的重要议题。受存在现象学影响,人文地理学现象学者着重从人之整体性经验出发,探究人地之间存在何种具体关联问题,普遍强调人与地方之辩证关联,即人参与到、内嵌于地方之中,同时地方构成人之存在的根本生境。此外,在民俗学与人类学内部,学者以景观(landscape)视角作为切入点,分析人及其文化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人与地方之复合性关联,引发诸多有待进一步思考的学理性问题。其中,如何透过特定的文化事实,来理解人与文化、文化与地方、人与地方之多重关系和纵横联系,成为学界亟待回答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丰富和深化我们对人地关系的认识与理解,而且对维续文化多样性和巩固非遗保护实践有所助益。本文着重以思南花灯为研究对象,围绕文化生态、生活景观以及地方生机等内容展开经验叙述和学理分析,以期回答上述问题。
一、文化生态:构造与位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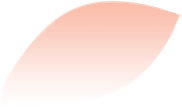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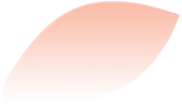
某一文化的产生、演变及维续与其所处的整体性文化生态相关联。若要认识与理解特定文化,则需窥探与剖析其所属的文化生态境况。何为文化生态?学者基于不同视角作出差异性回答。黄永林指出,“文化生态是指由构成文化系统的诸内、外在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态关系……在一定历史和地域条件下形成的文化空间,以及人们在长期发展中逐步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艺术表现形式,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和充满活力的文化生态”。由此可见,文化生态兼具自然面向和人文面向,兼顾人及其文化与自然和人文之间的交互关系。思南花灯是集歌唱、戏曲、杂技、纸扎、民间吹打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包含花灯小调、花灯舞蹈、花灯小戏等内容,其根植于思南地区由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人文环境统合而成的文化生态系统,具有鲜明的地方性特征。
(一)自然生态环境
“依河而兴、山川纵横”是思南县境内自然生态环境的总体概括。这一自然基础影响着生活于该地区的民众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等内容,形成具有地方性特征的文化形态。
1.“依河而兴”
乌江贯穿于思南县境内,为两岸民众在生活用水、农业灌溉、渔业捕捞、商业贸易等方面提供丰富资源。得水利之便,思南地区呈现出人来客往、资源融汇等局面,逐渐形成兼收并蓄的思南码头文化,由此思南成为乌江边上重要的商业城市。随着人口的流动与聚集,巴蜀文化、中原文化在思南地区得以扎根发芽。来自巴蜀、江西一带的商人在此地开号置户、安家定居,相继组建公会,修建会馆,搭建戏台,其中思南豫章家会(万寿宫)戏台仍是当前花灯表演与交流的重要场所。

受“因河而兴”的历史过程影响,当地人形成一种关于“水”的观念,即水是万物之源。在思南,当地民众在正月里跳花灯请神、送神时,都要到当地的水边(河边或水井边)请水,请求神明解除苦难和施予祥瑞,保佑整个村寨的吉祥及花灯队活动的顺利进行。在花灯唱词中,有关该地区的农事劳动、节令气候等内容也得以充分展现,形成一种时序体,即“以月、以季、以更等计时单位分节歌唱之体式”,展现着当地民众对于岁时节令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关系的认知与理解。如花灯小调《小采花》,唱词内容完整地叙述了不同月份中,植物的生长和民众的生产安排情况,展现受自然节律影响,当地民众的时间意识及规范生活方式。花灯艺人通过反复传唱相关内容,将自然生态、岁时节令以及生活方式相勾连,让人们理解作为文化载体的花灯所蕴含的丰富智慧。
2.“山川纵横”
思南地区属于喀斯特地貌,境内山地、丘陵交错复杂,平地可耕地面积少,人们在精神层面寻求保障与支持,从而催生了祭祀土地神的传统。明朝时期,思南地区便设有土地祠。人们为祈求来年继续得神灵保佑,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春节,各村各寨由德高望重的长者牵头,组织爱好花灯艺术的村民举行各式各样的迎送“土地爷”的花灯表演活动。
受极具多样形态的地形分布影响,思南地区境内的花灯也呈现出明显的地方特色,尤其是丝弦调,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如花灯歌曲《思南姑娘大脚板》中“思南姑娘大脚板。脚板大嘞大脚板,上坡坡来下坎坎;进屋见得公婆的面,出门过得媒人的眼”,诙谐生动地赞扬在思南地区起伏不平的地形条件下,思南姑娘的勤劳朴实、艰苦耐劳的品格,以及山区民众的健康审美观。
此外,思南盛产茶叶和竹子等地方物产。基于长期的采茶劳作活动,以“采茶”为主题的花灯戏曲得以创作,并衍生出《采茶·采古人茶》《采茶·四书茶》等结合民间故事和典故的采茶调,以及诸如《上茶山》等兼具旦角、丑角的民间小戏。得天独厚的竹材料为花灯的创作及花灯道具的准备提供素材。
(二)历史人文环境
在思南地区,生活于此的各族民众创造出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基于自然生态环境下的农耕、商贸等文化所孕育的思南花灯,伴随民族交融、文化交汇、社会交往互动,不仅呈现出多元文化融合的风貌,而且承载着地域历史与社会记忆,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形态。
1.民族交融
历史上的思南历经了从郡县制、经制州、大姓管理时期的时为经制时为羁縻的“土流间治”,到元末明初独立的土司管辖,明初思南宣慰司废除后的“土流并置”。无论哪一时期,思南地区始终在历代中央王朝的统治范围内,始终与中央王朝保持着臣属关系,尤其在元末独立于思州建置以后,思南地区开始与明、清中央王朝保持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逐渐与中央王朝保持一致。
清末民初,“地方募集资金请湖南辰河戏班来唱戏”,“川戏班来县在万寿宫唱川戏”。1946年至1948年间,许多京剧爱好者“在府城城隍庙”“永祥寺”等戏台频繁演出。随着多民族交往交流的日渐频繁,大量因商业贸易活动而迁入思南的移民,将辰河戏、川戏、京剧等艺术形式带入思南地区,一改“过去要逢年过节或修庙神会才请戏班唱戏的状况”,促进了花灯艺人商业意识的增强与审美观念的变化,吸纳了多元的艺术形式元素内容并融入花灯的表演中,花灯也由“花调子”转化为具有折子戏形式的“花灯戏”,具有职业性的花灯班子、花灯队也成立起来。
2.娱神-娱人
明朝时,大量戍边、屯垦的军队及各地移民进入贵州,推动贵州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影响了“社火”中的花灯活动从内容到形式的转化。花灯从祭社礼仪中分化出来,逐渐形成较为独立的艺术品格。花灯的演绎由原来无偿迎送“土地爷”、祈求神灵保佑,逐渐转化为向当地官府、驻军、商铺及各家各户拜年祝贺,受拜贺的一方,则以钱、米答谢跳灯的艺人以图开年大吉。这时的思南花灯,实现了从主要以酬神为目的到以娱神、娱人为目的转化,并演变为具商品化雏形的民间艺术。
花灯演绎是由灯队的灯头带领一二十个玩灯的人手持花灯牌灯、高灯、茶灯和宝宝灯,涌向接了“花灯奉贺”的帖子的人家唱灯。过年期间在城乡各地举行的群众花灯表演活动,不仅是集体娱乐狂欢的行为,也成为地方社区集体参与的活动,因此花灯也就必然具有凝聚社区民众生活的意义。
二、生活景观:民俗与时代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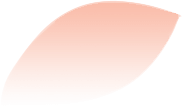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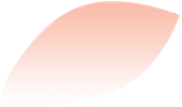
景观主要指涉“作为主体的人对周围环境的主观认知、感官体验和具体实践,以及人与特定空间和地方之间的经验性关联”。思南花灯的应用范围从年俗节庆扩展为日常生活,人与花灯之关联也从神圣性空间转向更为世俗性的生活空间,由此生成一种动态性的生活景观。

1.春节中的人与花灯
春节期间,跳花灯是思南地区的传统习俗。清初时,花灯歌舞以“采茶”的形式在社火活动中出现。上元时节的“彩戏”及迎春时的“台阁戏”,均是花灯戏的雏形,用以酬神还愿,将“戏”作为与神交流之媒介。思南所在地铜仁市,毗邻湘西麻阳,唐代同属锦州卢阳郡,据《麻阳县志》引述旧志,“每年上元初至中元十五为灯火佳节……有赋古而扮戏者”,说明当时的元宵灯节游乐活动就已出现了两人载歌载舞、一唱众人合的花灯歌舞戏形式,因此,思南民众跳花灯的习俗,至少从明代就已形成并得到广泛流传。
正月里,花灯队挨家挨户地对接帖子的人家进行走访表演,观众群体不仅限于当户人家,还有沿途跟随看戏的当地民众。浩浩荡荡的观众队伍跟随灯队穿梭于村寨间,花灯队会根据主人家的职业或诉求选择相对应的恭贺曲调,在不间断的观众围观和注视下,花灯队既要演绎出符合主人家心理预期的高规格的表演,又要避免重复造成观众审美疲劳,会尽量不断增减或改变内容,或以不同的表现方法来增加新鲜感以吸引观众。这就极其考验花灯队的知识储备、即兴反应及团队合作等能力。
节日因其高度的公共性、有组织性及历史传承性尤其适用于文化记忆的储存与交流。长期以来的文化沿袭,让思南人有了春节跳灯的传统。虽然思南各乡镇玩花灯时间长短不一,但都不约而同地选在过年期间,在岁首农闲之际用唱花灯、看花灯的方式庆祝丰收,为来年祈愿。这是思南人对多层次农业社会秩序构建、对宇宙观、自然观、价值观的直接表述。这种时间选择与文化传统背后蕴含的和谐统一、相辅相成等传统哲学思想,实际展现的是思南人共同知识框架体系内的叙事逻辑。
2.花灯艺术的时代化
20世纪50年代,在中共中央“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的座谈会召开后,贵州省文化部门开始对民族民间戏剧展开普查,文艺工作者深入农村,系统地收集散落在各地的花灯资料,创作了一些花灯剧目,并开展了各种形式的花灯汇演。
在此之后,思南花灯艺人受邀登上各级舞台。原本来自乡土的花灯被纳入新时期的文化体系建设中,在土地改革宣传队的带动下,将时事政策与花灯相结合,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各个场镇及村寨巡回演出,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用花灯表演的形式,宣传到广大人民群众。在政策引导下,花灯艺人投入空前的创作和表演热情,用丰富的花灯音乐、歌舞形式,用细节、用人物塑造和感情交锋,给观众以启蒙与启示,为花灯注入了新的时代记忆与烙印,通过艺术形式的创新,使之成为更具感染力的大众艺术。
1993年,思南县许家坝镇被贵州省文化厅授予“花灯艺术之乡”的称号。2004年,在政府与社会人士的努力下,思南举办了“首届花灯艺术节”,各乡镇的花灯队伍齐聚县城,重现了过去“人人跳花灯”的繁荣景象,新创作的花灯歌舞《思南姑娘大脚板》成为当地脍炙人口的歌曲,在央视音乐频道“民歌中国”上展演。后来,思南县还连续举办花灯艺术节,形成“艺术节”品牌效应,持续营造了思南人“爱跳灯”的文化氛围。
2006年,“思南花灯戏”被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开启了非遗保护的新发展历程,花灯艺人积极加入非遗传承的行列,花灯也逐渐跳出乡土社会,走向公众视野,还通过非遗进校园的方式,融入地区人才培养体系中,扩宽了花灯的传承范围。2008年,文化部授予思南“中国民间文化(花灯)艺术之乡”的荣誉,花灯成为思南人引以为豪的地方名片。2017年3月,思南县花灯艺术家协会成立,花灯爱好者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地方各级政府也在不断以“花灯”为主题元素,开展各类健身、文艺汇演等活动,如“百姓大舞台·花灯擂台赛”“许家坝镇花灯·龙灯齐聚闹新春”等,更是用各类宣传平台拓宽花灯的新传播渠道。为保持思南花灯的生命力,思南县还持续创新花灯艺术展演形式,将“全民健身”的理念与花灯歌舞艺术结合,持续举办“思南县花灯健身操大赛”,全县各地组织队伍踊跃参加,形成“花灯与健身”结合的新形态。
花灯的展演方式从春节期间的“人神共在的狂欢”逐渐演变成今日通俗化、日常化的花灯歌舞艺术。通过非遗保护,花灯各级传承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荣誉感和责任感。通过花灯艺人不断与时俱进地创作与传承,花灯的群众基础不断扩大,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花灯之乡”的命名,也使得参与传承与共享的思南民众产生了身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花灯也在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振兴等时代命题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地方生机:一种复合连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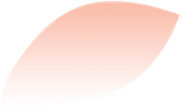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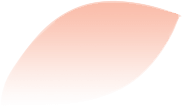
花灯勾连着当地人与人、人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多重联系,集中体现在地方记忆与认同的建构方面。在思南地区,当地人将花灯视为重要的生活内容。花灯涉及思南人的信仰体系、方言运用以及生产生活等社会文化意涵。花灯的演绎在以花灯为中心的民俗生活实践中建构个体身份认同,与此同时,花灯也会在花灯演绎者形成自我价值认同的基础上,将不同的“我”凝聚起来成为“我们”,其对内让个体对“我们”产生认同与归属感,对外则能跨越民族边界、确立区域文化边界。
(一)思南花灯的授艺方式
花灯的传承路径呈现出多元主体参与的复合型文化赓续机制,主要体现为家族传承的代际传播及在社会交往的观演过程中习得。传统花灯通过家族式口传身授实现技术谱系的纵向传递,不仅承载着地方性知识的历时性延续,更构建起代际文化对话空间;就社会交往层面而言,花灯通过岁时节庆的仪式化展演,创造了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突破家族、年龄、阶层等限制的文化联结场域。
1.家族传承
在传统花灯艺术传承谱系里,花灯艺人往往选择以家传方式挑选传承人。笔者的几个主要访谈人回忆学艺经历时,很多都提到最早对花灯的认识缘于爷爷、外公等长辈的传唱。笔者在调研中了解到,许多通过家族传承习得花灯的艺人会强调自己“未经过训练”“没专业学习”来佐证其与生俱来的花灯天赋,将花灯演绎归结为与说话、走路一样无需刻意学习、训练就能习得的技能。
花灯的传承过程,不仅是花灯艺术的承袭,更是亲情、情感的传递。受家族长辈的影响,艺人们在世代间传承和延续着同样的兴趣爱好,从事着祖宗传下来的文化事业。对任何一个从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以家族和村落为主要生活空间的艺人而言,血脉相连的家族传承及村落花灯氛围的熏陶和影响是他们对花灯产生兴趣的最初动因,也是艺人学艺的初级途径。

2.“灯窝窝”式观演习得
花灯流传的传统村落与花灯世家相似,每逢春节,村落里便开展“跳灯”活动,为村民提供集体传承的机会,当地人把这样的村落称为“灯窝窝”,如思南的许家坝舟水村、坝竹村等。一个被称为“灯窝窝”的村落,浓郁的演艺氛围在潜移默化中熏染了村民对花灯的兴趣而最终培养出大量的花灯艺人。在“灯窝窝”的生态环境下,村民中任何一员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同时也造就了各色灯艺历史传承与社会传播。在传统的跳灯活动里,“灯窝窝”里的村民集体出动,通宵达旦地狂欢,不论性别、年龄,不论文化背景,人人都可即兴编唱,个个都能高声附和。
通过调研发现,不论是排练还是演出,只要锣鼓声响起,都会引起村民围观,他们饶有兴趣地看完演出,时不时还会与花灯艺人形成互动。“灯窝窝”里浓厚的演唱和传承氛围,对孩子兴趣的养成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培养了在这里成长起来的每个人对花灯的兴趣和亲切的感觉,以及为数不多的以兴趣为导向,获得传统戏剧相关专业学习的花灯艺人。
从大部分艺人的学艺经历看,家族和村落的演艺氛围对其起到启蒙和兴趣培养的作用,人们在唱词、曲调和形体动作中,熟悉花灯表演的程式和角色。对普通民众而言,这一过程把他们培养成花灯传统的接受者和传承者。对于艺人来说,这为花灯的业内传承奠定了基础。
(二)花灯观演中的认同建构
在花灯观演过程中,观众既是花灯创造的参与者,还以一定的方式影响花灯艺术呈现乃至于功能转化的意义和性质;花灯的观演,让每个欣赏者和每个创作演绎者融会在一起,形成集体体验的激荡。
1.知识谱系的共享
思南花灯之所以能够浸润到思南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大众化的文化娱乐形式,不仅因为它通过对精选的历史故事、人物故事的反复叙述,构成民众共同拥有的系统知识谱系,而且因为其中蕴含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能够获得最大多数观众的认同,其中运用的民众熟悉的叙述模式与情感表现手法,也是引起观众共鸣的关键。
思南花灯包含当地民众生活生产经验、历史人物故事、富谜语性的趣味盘问、“求吉趋利”的祝愿、儒学教化意蕴、男女情感、时代事件等,这些元素构成了思南民众熟知且共享的庞大而复杂的知识谱系,在欣赏花灯队演出时,民众并不需要费力就能在音乐的配搭下分辨唱本里明白晓畅的韵文,又能第一时间获取熟悉的地方土语中最富机智的插科打诨,这种信息的传递并非单向的,而是一种互动式的交流,观众的反应,如掌声、喝彩声或情感上的共鸣,又反过来影响表演者的发挥,强化了知识传播的效果,进而促进了思南花灯的传承。
2.美好祝愿的送达
在思南,正月灯队到各家各户“玩灯”,是为在灯神的庇佑下为他们送去寿元、财富、平安等方面的美好祝愿。在平时,凡有祝神消灾、治病求子、发财升迁等许愿者,也可请灯队到家里进行许愿酬神。许愿者通过口头向灯队表达愿望,让其向灯神转达祈求意图。在祈求的愿望得以实现后,许愿者会专门邀请灯队到家里举办“还愿”的酬谢仪式,期望通过“仪式”与神灵建立联系,以报恩祈福。通过“许愿”“还愿”活动,许愿的家庭与灯队围绕“愿”
做出努力,并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讲诚信”“知恩图报”的心理贯穿始终,成为共同心理底色。花灯队存在的重要意义在于为民众建立了一个与神对话的平台,民众可将自己的诉求通过仪式活动与神灵进行交流,以达人神互助、互惠的目的。
“请灯”往往是建立在民众对某一灯队的专业性充分信任的基础之上。在“还愿”仪式上,灯队成员共同扮演了还愿主家代言人的角色,齐心协力表演,替主家向灯神传达祛灾祈福、继续求得福佑的心愿。主家也充分相信,集美妙歌舞与能说会道于一身的花灯艺人能与灯神沟通,证明自己的虔诚敬奉,从而获得心愿的灵验与内心的安宁。
总之,花灯艺人及团队,花灯灯队与观众,在花灯的观演活动之中,确保了花灯戏所承载的知识谱系得以延续和发展,使其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都能保持活力;灯队将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盼以艺术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在观演过程中,观众能够轻易地识别并理解这些蕴含在戏中的美好寓意,从而在情感上与表演者达成共鸣。这种基于共同文化认知的情感共鸣,为观演双方建立信任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过程对于地方文化的传承、社会凝聚力的提升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三)花灯文化记忆中的交融
思南花灯的唱词文本里蕴含思南地区各民族共有生活方式、共认价值取向、共享文化符号、共写历史经历等文化记忆的内容,是思南地区各民族民众长期积淀达成的心理共识。
1.岁时节令与农耕文化
思南花灯文化记忆中蕴含着对自然时间的认知。作为根植、生长于多民族长期共同铸造的农业社会中并存在于现代的活“纽带”,思南花灯戏唱词文本里多为传递节令气候的时序体,以满足民众不误农时的自然经济需要。花灯戏中浓缩的大量农事劳动实践,取材于现实生活,展现着各民族对岁时节令系统的认知与把握,通过传递与农耕文明相关的文化记忆,为保持着同一生产方式的文化认同延续性提供依据,也谱写了思南各民族民众对区域乡土社会的体悟。
2.历史记忆与价值遵循
思南花灯的文化记忆熔铸了对历史回忆的感悟。其唱词文本既保存和延续了思南花灯戏的来源传说,是历史上思南民众对历代中央王朝、中华民族身份的理解与认同;还将地方与国家真真切切发生的历史融入其中,在不断重构着过去、不断地与时俱进阐释着当下的过程中,铭记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同仇敌忾共御外敌、荣辱与共共建美好家园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思南花灯唱词文本里运用大量中华民族共享性的文化符号,如脍炙人口的故事传说、历史及虚构人物形象,构筑了活态化审美生境,辅以戏剧情景与表演叙事,直观地向观众传达文化记忆;思南花灯里记录了思南民众长期以来崇文尚儒的价值观念与实践,既表达了历史上思南地区多民族民众对历代封建王朝儒家思想正统性的维护与实践,又展现了集体所有成员秉承的具有约束力的共同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谱系。

思南花灯唱词的文化记忆把艺人与观众的记忆生活和生活记忆交互共融联系在一起,是各地区对于以往经验的观念性、文字性凝聚,源于国家话语体系作用下思南地方性记忆的整合,是花灯创新发展的动力,在花灯的传唱与演绎中,共享这一文化传统的人群在文化记忆的基础上形成具有共有生活传统、共认价值观念、共盼美好愿景的有机共同体,共同发展与繁荣了地方文化生机。
四、结 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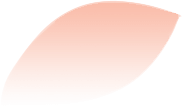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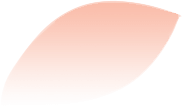
“江河蜿蜒”“山川纵横”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及地方语言和信仰体系等历史人文条件,共同构成思南花灯的文化生态,并成为花灯创作与表演的文化资源。换言之,多民族得以依存的自然生态与多民族民众创造的人文生态共同成为思南花灯发生发展的背景与根基。
思南花灯的艺术实践基于乌江河畔自给自足环境中多民族民众文化娱乐生活需要。在文化实践过程中,人与花灯同构的生活景观展现在不同时序、多种场景、多样唱词以及多元形式等方面。在过年和喜庆场合中,各民族民众以“思南花灯”神人交互的趣味表演进行互动,由艺人间的艺术切磋、团队间的互相成就、艺人及观众间的互动配合、观众间的共同话语等内容所构建的展演场域里,呈现的是以花灯为媒介的、各民族民众共同构合形成的地缘、情缘、趣缘共同体。在思南花灯“以表演为中心”的娱乐活动中,社群共同体的认同是思南花灯生发的坚实基础。
思南花灯的持续性展演及其蕴含的文化基因交融成为县域社会文化的生机之力,在呈现地域文化生态和构建民众生活景观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作为花灯传承的主要载体,花灯艺人从身体内部与外部空间交织构筑民族生活情景互释的文化符号,再通过花灯队相互配合的集体身体实践,将思南地区民众的宇宙观、生命观、身体观代代相传,因而成为承续区域文化、沟通集体内外的符号象征。思南花灯以艺术实践的方式呈现了当地的生活和文化的传统,将中华民族共有的生活生产知识融入其中,通过传递多民族民众对共同生产实践和民俗的普遍认同与受众产生共鸣,又不断有效地形塑民众的生活生产实践,在此基础上强化了花灯戏艺人、群体及受众对于共同区域内各民族的认同感。
简言之,地方文化的产生、延续与特定的文化生态息息相关,后者由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人文条件交织构成。在地方文化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当地人借身体感官及其思维认知之力,与所处的文化生境发生关联,进而生成一种动态性生活景观。随着地方文化的持续性实践,地方生机以一种复合衔接的方式得以展现,并与文化生态和生活景观形成有效联通。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