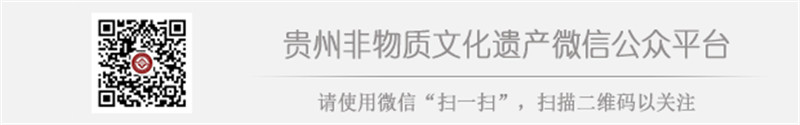作者简介

李宝贵,文学博士,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国际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中文教育、中文国际传播和语言政策与规划。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配合支持更多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理论建构与实现路径研究”(22BYY154)、国家语委重点项目“中华语言文化国际传播的挑战与对策研究”(ZDI145-37)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讲好中国故事、架好互通桥梁、塑好中国形象的重要载体,对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具有重要价值。当前,非遗海外传播的多元主体持续拓展,受众数量快速增加,传播内容日渐丰富,传播媒介不断创新,传播效果逐步显现。非遗海外传播也面临着传播主体协同度有待深化、传播客体区分度有待细化、传播内容记忆度有待强化、传播媒介接受度有待提升、传播效果满意度量化有待加强等现实困境。基于此,提出非遗海外传播困境的纾解策略:构建非遗海外传播共同体;提升非遗海外传播的精准度;讲述有温度的中国非遗故事;以数智技术赋能非遗海外传播;构建非遗海外传播效果评价体系。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海外传播;中国故事;传播媒介;传播共同体

引言
在巴拉圭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9届常会上,“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顺利通过评审,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作为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活态性和民间性的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明百花园中璀璨的瑰宝。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所指出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2]。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海外传播,不仅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有效途径,也是架设互通桥梁、践行交流互鉴的生动实践,更是塑造中国形象、展示中国智慧的迫切需要。我们要用心讲述有温度的中国非遗故事,努力传播好中国声音,积极践行交流互鉴,充分展示中国智慧。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研究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在第十部分“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中就如何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提出具体要求[3]。全面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必须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中文国际传播是我国国际传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与桥梁[4]。提升中文国际传播效能是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重要一环。广义的中文国际传播既包括中文的国际传播,也包括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5]。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海外传播的重要载体。目前在国际中文教学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重要性的认识还不足,其开发利用还有很大空间[6]。要充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全面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海外传播,提升中文国际传播效能,进而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7]。《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8]。综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世界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知识、技能、艺术、民俗等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实践和精神内涵。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海外传播研究已经引起学界关注。现有研究对国际中文教育促进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提升策略[9]、国际中文教育用中国文化和国情教学参考框架[10]、中国文化教学新思路[11]、中国概况教学原则[12]、非遗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应用[13]、与非遗海外传播相关的期刊论文研究现状与展望[14]、国际中文教育视域下的非遗跨文化传播[15]、中国“非遗”出海的学理依据与模式[16]、国际中文教育促进中华语言文明传承传播的内在逻辑与优化路径[17]、中华民族文化共同性及其生成逻辑[18]、非遗传承人传承动机及保护政策[19]、传播学视域下非遗海外传播的路径[20]、文化遗产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促进作用[21]、体育非遗海外传播叙事体系[22]、体育非遗海外传播路径[23]、非遗视频海外传播的叙事模式和话语体系[24]、徐州市非遗翻译与海外传播[25]、传统工艺海外传播[26],以及数智时代成都市非遗海外传播路径[27]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这些成果为开展非遗海外传播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然而,作为我国国际传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从中文国际传播视角阐释非遗海外传播的现状特征、现实困境与纾解策略,尚未引起学界的重视,相关研究仍有待深入。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海外传播的现状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28]。我国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后,与非遗海外传播相关的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
(一)非遗海外传播的多元主体持续拓展
非遗海外传播主体的覆盖度是指非遗资源拥有者被非遗海外传播主体覆盖的数量,是衡量参与非遗海外传播的非遗资源拥有者数量多少的重要参考。非遗海外传播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多元主体。
1.国务院组成部门作为传播主体开展非遗海外传播
国务院组成部门作为传播主体开展非遗海外传播可起到引领示范作用,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统筹协调,合理配置非遗资源,广泛拓展非遗海外传播主体的覆盖度。2007年4月,由原文化部(现为文化和旅游部)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节”首次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29]。此次活动不仅开启了我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开展非遗海外传播的序幕,还在全球范围内为各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开展非遗海外传播提供了有效范式。
2.地方各级政府作为传播主体开展非遗海外传播
地方各级政府作为传播主体开展非遗海外传播,可最大限度地传播具有地方特色的非遗项目,有效带动所在地区的各省、市、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及其弟子参与非遗海外传播,深入拓展非遗海外传播主体的覆盖度。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下文简称“非遗节”)创办于2007年,每两年举办一届。从2007年5月至2023年10月,“非遗节”已成功举办了八届。在筹办2009年第二届“非遗节”时,原文化部(现为文化和旅游部)根据成都市的建议,邀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与主办,并由此形成主承办的定制,“非遗节”也成为国内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持续参与主办的唯一节会活动[30]。第八届“非遗节”由文化和旅游部、四川省人民政府和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办[31]。迄今为止,“非遗节”已成为全球范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重要节会。
3.社会组织作为传播主体开展非遗海外传播
社会组织是非遗海外传播过程中政府和个人之间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对有效拓展非遗海外传播主体的覆盖度具有重要作用。2006年8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挂牌成立。无论是首次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节,还是一开始由地方政府主办的“非遗节”,作为承办单位之一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都是重要的非遗海外传播主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是根据中国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署的协议,在北京成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国际机构。自2012年2月成立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结合的培训方式持续开展非遗海外传播。
4.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作为传播主体开展非遗海外传播
作为非遗资源的主要拥有者,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及其弟子是非遗海外传播主体的中坚力量。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及其弟子是否积极参与非遗海外传播会对非遗海外传播主体覆盖度产生重大影响。2018年2月,由原福建省文化厅(现为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马来西亚惠胜集团联合举办的闽都文化专题图片展和非遗实物展在马来西亚马六甲市的“福建文化海外驿站”拉开帷幕。福州软木画代表性传承人陈君锟为此次展览带来了精心创作的《桂林山水》《江南春晓》《苍松》等软木画作品[32]。2024年6月,“诗画江南——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在毛里求斯中国文化中心成功拉开帷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琵琶艺术(平湖派)代表性传承人黎庆慧演奏了平湖派琵琶曲目《平沙落雁》[33]。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罗晨雪、胡维露等上海昆剧团的演员首次携昆曲全本《牡丹亭(精华版)》来到法国,在法国波尔多国家歌剧院、巴黎蕾博拉戏剧院开启跨越国界的文化之旅[34]。作为非遗传承者与传播者,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及其弟子在非遗海外传播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5.海内外非遗爱好者作为传播主体开展非遗海外传播
海内外非遗爱好者是非遗海外传播主体的后备力量,部分海内外非遗爱好者也可成为非遗海外传播的主力军,进而提高非遗海外传播主体覆盖度。“金石篆刻(西泠印社)”于2006年(第一批)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国篆刻”也于2009年9月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2007—2012年,李岚清篆刻书法艺术展相继在俄罗斯、法国、印尼和英国等地的重要文化场馆举办海外巡展。2024年3月,“中国寻根之旅”南音特色春令营(福建泉州营)圆满收官。在泉州南音传承人的口传心授下,22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华裔青少年学习南音乐谱乐器,读懂南音曲调,甚至还能哼唱几曲简单的南音,成为南音文化的传播者[35]。综上,海内外非遗爱好者既是非遗资源的拥有者,也是非遗海外传播主体的后备力量。
6.中文教师和志愿者作为传播主体开展非遗海外传播
依托孔子学院、孔子课堂、中文工坊、鲁班工坊等平台,国际中文教师和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在非遗海外传播中承担着重要角色,是进一步提高非遗海外传播主体覆盖度的重要力量。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在《关于开展2025年“国际中文日”文化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指出,项目内容为“文化遗产”的选题要围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名录》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世界文化遗产(含非物质文化遗产),讲述中国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成功实践和生动故事,彰显人类文明的多样性[36]。
(二)非遗海外传播的受众数量快速增加
非遗海外传播客体的参与度是指海外受众在非遗海外传播过程中的参与程度,是衡量海外受众对非遗海外传播的认可度和满意度高低的重要参考。以“请进来”和“走出去”方式开展非遗海外传播是提升非遗海外传播客体参与度的有效途径。
1.海外受众参与以“请进来”方式开展的非遗海外传播
当前,我国以“请进来”方式开展非遗海外传播的传播客体参与度逐年提升。从2007年5月至2023年10月,“非遗节”已成功举办了八届。据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的统计:前七届“非遗节”累计开展2000余场活动,共有9000多个非遗项目参展,600余支表演队伍参演,135个国家(地区)和非政府组织的4000余名外籍嘉宾和国内4万多名代表参加,2000多万市民和游客现场参与[30];第八届“非遗节”邀请来自国内和全球47个国家(地区)的900余个非遗项目、5000余名嘉宾及传承人,共襄非遗盛会[37]。“非遗节”以“请进来”方式有效开展了非遗海外传播,扩大了非遗海外传播的海外客体参与度。
2.海外受众参与以“走出去”方式开展的非遗海外传播
目前,我国以“走出去”方式开展非遗海外传播的传播客体参与度显著提升。2025年“欢乐春节”全球启动仪式暨“欢乐春节 五洲同欢”演出1月25日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38]。从2017年起,湄洲妈祖祖庙先后组织妈祖金身巡安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吸引了当地华侨华人和妈祖敬仰者近千万人次参与[39]。妈祖信俗已传播到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两亿多民众所崇拜并传承至今。
(三)非遗海外传播的传播内容日渐丰富
非遗海外传播内容的可见度是指非遗海外传播过程中传播内容在世界范围内被传播客体看见的可能性和程度。作为履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约国义务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积极推进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项目的相关工作,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见度。非遗海外传播内容的可见度是衡量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项目工作和多元主体开展非遗海外传播活动效能的重要参考。
1.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工作屡创佳绩
数量很多、门类齐全、内容丰富、意蕴深厚的非遗项目不仅展现了我国深厚的文化底蕴,也为非遗海外传播提供了丰富的传播内容。中国的昆曲、古琴艺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和蒙古族长调民歌于2008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截至2008年11月8日,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项目共计4项。截至2024年12月5日,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项目共计44项,总数位居世界第一。此外,我国共有国家、省、市、县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超过10万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的项目共计1557项。国家、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的项目是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名册)项目的后备力量。
2.多元主体开展了丰富多彩的非遗海外传播活动
非遗海外传播的多元主体开展了丰富多彩的非遗海外传播活动,如在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开展蔚县剪纸传播,在澳大利亚开展福建木偶戏传播,在西班牙开展湖南杖头木偶戏和湖南皮影戏传播,在巴黎举办的第28届世界文化遗产展览会上开展龙泉青瓷传播,在毛里求斯开展琵琶艺术(平湖派)传播等。此外,在海外任教的国际中文教师和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组织的非遗教学和非遗体验活动也是快速提高非遗海外传播内容可见度的重要途径。
(四)非遗海外传播的传播媒介不断创新
非遗海外传播媒介的新颖度是指非遗海外传播过程中传播媒介的新奇和别致程度,是衡量能否有效吸引海外受众关注的重要参考。从动作角色扮演游戏《黑神话:悟空》中的“陕北说书”到使用虚拟现实头戴式显示设备体验“虚拟非遗”,从非遗实物藏品到非遗数字藏品,以数智科技赋能非遗海外传播既实现了非遗“活”起来,也实现了非遗“潮”起来。
1.数智化时代非遗海外传播借助新兴技术焕发新生
数智化时代的非遗海外传播利用全息投影技术、视觉融合技术、虚拟技术、3D技术等手段展示非遗,新兴传播媒介也应运而生。2023年,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科技创新孔子学院与大学视觉设计团队联动,策划开展了首次裸眼3D楼体秀活动。该活动借助全息投影技术和视觉融合技术,在哈德斯菲尔德大学的理查德·斯泰尼茨大楼表面进行光影投射,构建融合水墨画、传统建筑、汉字、皮影戏等许多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的虚拟场景[40]。2022年端午节期间,宜昌市文旅局与北京冬奥会视效总制作团队“黑弓BLACKBOW”联合开发“宜昌·端午”系列数字藏品,以“粽子”和“龙舟”等端午节符号为灵感,融合宜昌特色文化元素,通过极具想象力的创意组合,创造了两个系列共12款数字藏品,成为全国第一个上线的以端午为主题的数字藏品系列[41]。新兴传播媒介实现了非遗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已成为非遗海外传播的助推器。
2.现代影视作品与传统媒介合力促进非遗海外传播
现代影视作品与传统传播媒介的协同创新,为非遗海外传播开辟了全新路径。这种融合既保留了非遗的核心价值,又通过创新表达方式高效开展非遗海外传播。传统传播媒介在非遗海外传播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推动传统传播媒介焕发青春活力,与现代影视作品形成合力,为海外受众在选择传播媒介过程中提供更多选项。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文化和旅游部联合摄制的秉承“见人、见物、见生活”理念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和河南卫视“奇妙游”系列等可用于非遗海外传播的现代影视作品不断涌现。此外,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文创团队根据镇馆之宝“万善正觉殿天宫藻井”设计了天宫藻井冰箱贴。天宫藻井冰箱贴共分为五层图案,既可分开摆放,也可组合叠起;不仅能展示藻井不同部分的独特魅力,也能还原完整的藻井形态。天宫藻井冰箱贴正式上线后,受到了海内外收藏者的青睐。《非遗里的中国》呈现的“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营造技艺”与现实生活中的“天宫藻井冰箱贴”的相遇,践行了“见人、见物、见生活”理念,有效开展了非遗海外传播。综上,推动现代影视作品与传统传播媒介形成合力,促进非遗海外传播。
(五)非遗海外传播的传播效果逐步显现
非遗海外传播效果的认可度是指非遗海外传播效果被认可的程度,是衡量非遗海外传播是否达到预期目标的重要参考。
目前,每两年举办一届的“非遗节”已成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并积极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重要节会。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项目由最初的4项增至44项,项目总数位居世界第一。哈德斯菲尔德大学组织的首次裸眼3D楼体秀活动视频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的观看量逾20万,点赞量超1万余次[40]。目前,中医药已经传播到了196个国家和地区。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103个会员国认可使用中医针灸,29个设立了传统医学的法律法规,18个将针灸纳入医疗保险体系。政府间的中医药合作协议已签署86份,每年约有13000多名留学生来华学习中医药知识[42]。综上,我国各种门类的非遗海外传播效果已逐步显现。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海外传播的现实困境
2024年是我国批准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周年。20年来,我国非遗海外传播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面临着一系列现实困境。总结非遗海外传播的现实困境,可提出有针对性的非遗海外传播的纾解策略,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贡献力量。
(一)非遗海外传播主体协同度有待深化
非遗海外传播主体的协同度是指政府、社会组织、个人等多元主体之间在非遗海外传播过程中通过合作与互动实现的协同效应,是衡量多元主体能否高效开展非遗海外传播的重要参考。
目前,国务院组成部门之间的协同效应已完全显现。国务院办公厅于 2005年3月印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其中的附件2要求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2022年1月,国务院同意调整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职责和成员单位。联席会议由文化和旅游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网信办等20个部门组成,文化和旅游部为牵头单位。然而,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度却有待深化。如前所述,蔚县剪纸海外传播的主体为蔚县剪纸传承人,福建木偶戏海外传播的主体为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杖头木偶戏海外传播的主体为湖南省木偶皮影艺术保护传承中心,琵琶艺术(平湖派)海外传播的主体为平湖派琵琶艺术传承人。需要指出的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的剪纸包括剪纸(蔚县剪纸)、剪纸(丰宁满族剪纸)、剪纸(中阳剪纸)等56个子项,木偶戏包括木偶戏(泉州提线木偶戏)、木偶戏(郃阳提线木偶戏)、木偶戏(孝义木偶戏)等31个子项,琵琶艺术包括琵琶艺术(瀛洲古调派)、琵琶艺术(浦东派)、琵琶艺术(平湖派)等3个子项,但每个非遗项目内部各子项之间缺乏传播合力。综上,地方政府、各种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多元主体之间应通过合作与互动实现进一步深化协同度,高效开展非遗海外传播。
(二)非遗海外传播客体区分度有待细化
非遗海外传播客体的区分度是指非遗海外传播过程中对海外受众的区分程度,是衡量非遗海外传播过程中能否因材施教的重要参考。
目前,非遗海外传播客体区分度有待细化,“因材施教”理念在非遗海外传播过程中还没有落到实处:一是区域国别非遗海外传播研究与实践有待开展;二是当前非遗海外传播中的海外受众只包括一部分现实受众,而非全部现实受众,对潜在受众的关注度更低;三是对低龄海外受众的关注度较低;四是对不同民族、宗教习俗的海外受众的区分度有待细化;五是对不同职业的海外受众区分度有待细化;六是对不同教育水平的海外受众区分度有待细化;七是对不同学习动机和兴趣爱好的海外受众区分度有待细化。
(三)非遗海外传播内容记忆度有待强化
非遗海外传播内容的记忆度是指非遗海外传播内容在传播客体记忆中留下的印象和认知度,是衡量非遗海外传播效果持续时间长短的重要参考。
非遗海外传播要通过讲述有温度的中国非遗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践行好交流互鉴,展示好中国智慧,为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贡献力量。目前,非遗海外传播存在传播内容记忆度有待强化的问题:一是以传播主体宣讲的方式开展非遗海外传播,非遗海外传播内容记忆度有待强化;二是不注重文化“他性”和非遗交流互鉴的非遗海外传播,非遗海外传播内容记忆度有待强化;三是气氛好、效果差的非遗海外传播,非遗海外传播内容记忆度有待强化。
(四)非遗海外传播媒介接受度有待提升
非遗海外传播媒介的接受度是指传播客体对非遗海外传播媒介的接纳和认可程度,是衡量传播媒介能否精准满足不同受众群体需求的重要参考。
随着数智时代的到来,智慧化手段赋能非遗海外传播已成为新趋势。倘若对传播客体的区分度进行细化,就不能遵循“一刀切”原则在非遗海外传播过程中选取传播媒介。一般来讲,大部分海外年轻人对新事物适应性强、接受度高,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新兴传播媒介对这部分海外受众来说是合适的选择。然而,还有一部分受众群体习惯通过报刊、书籍、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获取、学习非遗内容,对数字化和智能化的传播媒介接受度较低。目前,存在重视新兴传播媒介,轻视传统传播媒介的问题。
(五)非遗海外传播效果满意度量化有待加强
非遗海外传播效果满意度,是传播客体对传播过程的感性评判,也是衡量传播是否高效的关键参考。当下,非遗海外传播效果主要以参与传播活动的人数作为衡量指标,秉持参与人数越多、传播效果越好的理念。但这一人数标准至今未得到量化,且对于传播主体、内容、媒介以及过程等方面的传播效果评价不仅稀少,同样亟待量化。非遗海外传播效果评价在操作细则、标准与评价体系等层面,都有待深入探究。总体而言,当前非遗海外传播效果评价仍处于粗放阶段。因此,需持续总结、探索与反思,实现从粗放型效果评价向集约型效果评价的转变。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海外传播困境的纾解策略
通过不断深化与拓展非遗海外传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为构建更有效的国际传播体系贡献力量。针对非遗海外传播面临的现实困境,非遗海外传播的纾解策略应构建非遗海外传播共同体,提升非遗海外传播的精准度,讲述有温度的中国非遗故事,以数智技术赋能非遗海外传播,构建非遗海外传播效果评价体系。
(一)构建非遗海外传播共同体
非遗海外传播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组织、个人等多元主体。政府不仅包括中国政府,还包括其他国家政府。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项目共计44项,其中2项是我国与其他国家联合申报的非遗项目,即我国与蒙古国联合申报的“蒙古族长调民歌”和我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在开展“蒙古族长调民歌”和“送王船”海外传播时,我国政府应分别与蒙古国政府、马来西亚政府构建非遗海外传播共同体,合理配置各种非遗资源并形成合力,高效开展非遗海外传播。各种组织包括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媒体、高校、智库和企业等。个人包括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及其弟子、国家公派出国教师、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海外本土中文教师以及海内外非遗爱好者等中国非遗资源拥有者。
首先,要建立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多元主体之间跨国、跨地区的合作与互动机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如何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提出具体要求,其中一个是“推动走出去、请进来管理便利化,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3]。构建非遗海外传播共同体,以“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方式开展非遗海外传播,扩大各国非遗交流合作,促进各国非遗交流互鉴,从而提升非遗海外传播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有效举措。
其次,开展体系化的非遗海外传播。我国非遗的体系可以概括为“生生遗续”。“生生遗续”为总体系,“六生”(生命礼仪、生态亲和、生计方式、生产技术、生业组织和生养制度)为次体系,每一个次体系中又有各自的核心元素(身体表述、自然生态、生活方式、生产技艺、行业组织和传承机制)[43]。要建立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机构组织和个人之间合作开展非遗海外传播的协同机制,要组建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机构组织和个人之间各展专长、互通有无的非遗海外传播队伍,共同构建非遗海外传播共同体。
最后,合理配置非遗海外传播过程中的各种资源。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机构组织和个人之间要开展合作与互动,形成合力后再开展非遗海外传播,以免出现气势不足、效果不佳的情况。相同类别的非遗项目往往有若干个子项。以琵琶艺术为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的“琵琶艺术”有3个子项,即琵琶艺术(瀛洲古调派)、琵琶艺术(浦东派)和琵琶艺术(平湖派)。倘若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琵琶艺术”不同子项之间的交流互鉴则可推动中国琵琶艺术的进步。要整合海内外各种资源,构建琵琶艺术海外传播共同体。
(二)提升非遗海外传播的精准度
从地理维度讲,我国非遗海外传播受众可划分为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大洋洲等不同区域的受众。从国别维度讲,我国非遗海外传播受众可划分为印度尼西亚、法国、加拿大、巴西、埃及、澳大利亚等不同国家的受众。从语别维度讲,我国非遗海外传播受众可划分为英语国家和地区、俄语国家和地区、阿拉伯语国家和地区、法语国家和地区、西班牙语国家和地区等不同语种的受众。从文化维度讲,我国非遗海外传播受众可划分为儒家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等不同文化圈的受众。从国际组织维度讲,我国非遗海外传播受众可划分为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受众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国际红十字会、国际足球联合会等非政府间合作组织的受众。从教育层次维度讲,我国非遗海外传播受众可划分为基础教育阶段、高等教育阶段和职业教育阶段等不同教育阶段的受众。此外,我国非遗海外传播受众还可划分为不同年龄、性别、民族、宗教、职业、学习动机、兴趣爱好等不同类型的受众。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44]。要按照非遗海外传播客体的国籍、年龄、性别、民族、宗教、职业、学习动机、教育水平等细化传播客体的区分度。根据不同的传播客体制定有针对性、体系化的非遗海外传播方案,设计、制作、编写并选取适合传播客体的非遗海外传播媒介,构建满足不同传播客体需求的具有规范性、可操作性的非遗海外传播效果评价体系。此外,非遗海外传播要积极争取非遗海外传播的潜在受众,并在一定条件下把非遗海外传播客体转化为非遗海外传播主体,为非遗海外传播行稳致远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讲述有温度的中国非遗故事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全人类共同的瑰宝。数量很多、门类齐全、内容丰富、意蕴深厚的非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体系的组成部分。非遗的海外传播不仅要注重非遗本身的真实性和逻辑性,也要结合当地文化讲述有温度的中国非遗故事,分享有中国特色的东方智慧。非遗海外传播内容注重文化“他性”,既可以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外高效传播,又表达了对传播客体所在国文化理念的尊重。花茶制作技艺(福州茉莉花茶窨制工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名录中的非遗项目。茉莉花茶飘香,情满福州鼓岭,习近平主席为讲述有温度的中国非遗故事起到了引领示范作用。
2023年6月28日,习近平主席向“鼓岭缘”中美民间友好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1992年,我邀请加德纳夫人访问鼓岭,帮助她完成了丈夫梦回故土的心愿。”鼓岭故事是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中美民间友好交流的一段佳话。1901年,在襁褓之中的美国人密尔顿·加德纳随父母来到中国福州生活,1911年全家迁回美国。加德纳先生一直想要再回中国故园看一看,但直到去世也未能如愿。在中国留美学生帮助下,加德纳夫人终于了解到丈夫魂牵梦萦的故园就是福州的鼓岭。1992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了解到这段感人的鼓岭情缘,邀请加德纳夫人访问中国。2012年,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时,在美国友好团体举行的欢迎午宴上讲述鼓岭故事,引发两国各界强烈反响[45]。面向不同的非遗海外传播客体,选取适合传播客体的中国非遗故事,可强化传播内容的记忆度并提高传播媒介的新颖度,以期在非遗海外传播过程中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
(四)以数智技术赋能非遗海外传播
传播媒介既包括报刊、书籍、广播、电视等传统传播媒介,也包括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中文联盟”数字化平台中的非遗资源、北京语言大学发布的“国际中文智慧教学系统3.0版”、H5互动游戏以及“抖音”“快手”“Instagram”等新兴传播媒介。需要指出的是,国际中文教育的教材和各类教学资源中应凸显非遗内容。非遗海外传播多元主体要持续关注受众对不同传播媒介的接受度,为不同的受众提供不同的传播媒介,进而在海外高效开展非遗传播。科技进步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然而智能手机和老年机并存却是市场需求的结果。面向不同类型的受众,非遗海外传播媒介要不断推陈出新,确保传播媒介能精准对接不同受众需求。人工智能赋能非遗海外传播,新兴传播媒介不断创新。科技是一把双刃剑,要促进传统传播媒介和新兴传播媒介并行发展,确保不同类型的非遗海外传播媒介能精准对接不同受众需求。面向海外低龄学习者的非遗海外传播,要利用趣味性和互动性强的非遗游戏软件开展非遗海外传播。面向海外年轻人的非遗海外传播,要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平台开展非遗海外传播。面向不能熟练使用数字化和智能化传播媒介的受众,要提供报刊、书籍、广播、电视等传统传播媒介。面向海外汉学家的非遗传播,要依托非遗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国际期刊开展非遗海外传播。
(五)构建非遗海外传播效果评价体系
受众对非遗海外传播效果满意,是非遗海外传播要达到的目标。满意与否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因此,要量化传播效果的满意度,构建科学、规范的评价体系。一是要构建非遗海外传播效果评价体系,增强传播效果的认可度,量化传播效果的满意度。二是要构建面向不同受众群体的传播效果评价体系,实现量化传播效果满意度目标。三是要构建科学、规范的非遗海外传播效果评价体系,并建立非遗海外传播效果评价的反馈机制。四是评价体系和反馈机制之间要形成高效良性互动,提高非遗海外传播效果的信度和效度。五是创建非遗海外传播效果评价数据库,从共时和历时两个维度分析非遗海外传播效果评价数据。六是开展非遗海外传播效果评价体系和反馈机制的学术研究,以科研促传播,进而实现量化传播效果的满意度,构建科学、规范的评价体系的目标。
结语
截至2024年12月5日,我国已有44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总数位居世界之首,彰显了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领域的斐然成就。然而,非遗海外传播领域仍存在诸多亟待深耕与拓展之处。本文全面梳理了非遗海外传播现状,涵盖传播主体的多元拓展、受众数量的快速攀升、传播内容的日益丰盈、传播媒介的持续创新以及传播效果的逐步彰显。同时,深入剖析了其面临的现实困境,诸如非遗海外传播主体协同度有待深化、非遗海外传播客体区分度有待细化、非遗海外传播内容记忆度有待强化、非遗海外传播媒介接受度有待提升、非遗海外传播效果满意度量化有待加强等问题。基于此,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纾解策略:一是构建非遗海外传播共同体,推动政府、社会组织及个人等多元主体开展跨国、跨地区合作,凝聚合力,高效推进非遗海外传播;二是提升非遗海外传播精准度,细化传播客体区分度,制定针对性传播方案;三是讲述饱含温度的中国非遗故事,融合当地文化,强化传播内容记忆点;四是借助数智技术赋能非遗海外传播,运用全息投影、视觉融合、虚拟技术等新兴媒介,实现非遗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五是构建非遗海外传播效果评价体系,量化传播效果满意度,为非遗海外传播筑牢坚实保障。
未来的研究应聚焦于以下关键领域:第一,应进一步深化对非遗海外传播效果的长期追踪与量化研究,构建更加完善且动态的效果评估模型,从而精准衡量传播策略的实际成效;第二,需聚焦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传播策略适应性调整,探索如何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实现非遗传播内容与形式的本土化创新,从而提升传播的深度与广度;第三,应加强对新兴技术在非遗传播中应用效果的研究,充分挖掘其潜在价值,不断拓展非遗海外传播的边界与可能性。通过持续努力,不断提升非遗海外传播效能,这不仅能够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与影响力,更能促进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互鉴,携手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