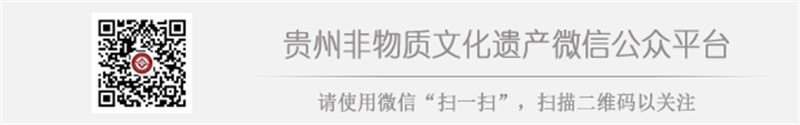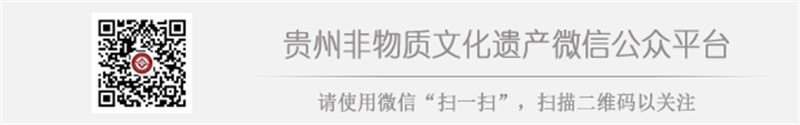非遗名录中贵州传统戏剧的类型、 特征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价值
(铜仁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铜仁 55430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清代以来湘黔桂边区民族民间戏剧文化交融历程研究”(项目编号:22BMZ060);铜仁学院 2022年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生态文明视域下武陵民族地区传统生态知识活化利用研究”(项目编号:trxyDH2208)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 侯有德,博士,铜仁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化遗产学和生态民族学;蒋欢宜,博士,铜仁学院教授、硕士 生导师,研究方向:西南民族文化和文化遗产学。
[摘要]:非遗名录中的传统戏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名录中的贵州传统戏剧种类丰富,涵盖少数民族戏剧、祭祀仪式性戏剧、傀儡戏剧、民间小戏四大类型。非遗名录中的贵州传统戏剧具有民族特色鲜明、原始古朴之风浓郁、交融态势凸显等特征,在增强贵州各民族对本民族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强化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贵州传统戏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在生产生活中创造的精神财富。截至2021年,在国务院公布的五批国家级(含扩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传统戏剧有246项,占项目总数(1842项)的13.36%,且已覆盖全国65%的戏剧剧种和样式[1]。传统戏剧也是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类型之一。在五批国家级(含扩展)非遗名录中,贵州省有109项代表性项目,其中传统戏剧类项目有14项,占项目总数的12.84%,仅次于民俗类项目和传统手工技艺类项目,排名第三。在五批省级(含扩展)非遗名录中,贵州省有785项代表性项目,其中传统戏剧类项目有50项,占项目总数的6.37%,仅次于民俗类项目、传统手工艺类项目、民间音乐类项目、民间舞蹈类项目,排名第五[2]。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非遗名录中的贵州传统戏剧不仅类型丰富、特色鲜明,而且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价值。贵州入选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的传统戏剧类型颇多,涵盖侗戏、布依戏、仡佬族滚龙戏、傩戏、撮泰吉、阳戏、端公戏、目连戏、文昌戏、梓潼戏、安顺地戏、石阡木偶戏、花灯戏、马马灯、茶灯等诸种。这些传统戏剧在表演形式、表演内容、表演媒介、艺术特征等方面既有相似性和共通性,又有差异性和独特性。根据本质属性和主要特征,可划分为少数民族戏曲剧种、祭祀仪式性戏曲剧种、傀儡戏曲剧种、民间小戏剧种四种类型。贵州是民族传统戏剧文化大省,境内的苗族、布依族、土家族、侗族、彝族、瑶族、白族、壮族、毛南族、仡佬族等民族均有自己的戏剧文化。在入选国家级(含扩展)、省级(含扩展)非遗名录的64项贵州传统戏剧中,少数民族戏剧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贵州少数民族戏剧就有侗戏、布依戏等。作为贵州民族传统戏剧中影响最大剧种之一的侗戏,有“滋润侗乡的甘霖”之美誉。侗戏以“嘎劲”“摆古”等侗族民间说唱艺术为基础,以侗族、汉族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为题材,以胡、铃、锣、鼓、琵琶和牛腿琴等为乐器,以“平调”“哭板”“仙腔”等唱腔搭配舞台表演[3]。经典剧目有《珠郎娘美》《梅良玉》《凤娇李旦》等。布依戏在布依族语中称“谷艺”,主要流传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兴义、册亨、安龙等地。布依戏是在布依族板凳戏和八音坐唱基础上融合汉族、苗族戏剧模式而形成的表演艺术,是贵州最古老的民族戏剧之一。布依戏用布依语演唱。传统布依戏的曲调有“长调”“官扮调”“二簧”“二六”。布依戏采用以生、旦、丑为主的传统角色扮演形式,演出程序一般包括开箱、敬老郎、点符浪、降三星、打加官、主戏、升三星、扫台、送老郎、封箱。经典剧目有《罗细杏》《三月三的木叶声》《胡喜与南祥》《金竹情》等。在入选国家级(含扩展)、省级(含扩展)非遗名录的贵州传统戏剧中,祭祀仪式性戏剧主要有傩戏、撮泰吉、阳戏、端公戏、目连戏、文昌戏、梓潼戏等。彝族撮泰吉虽为彝族的民族传统戏剧,但它本质上是一种祭祀仪式性戏剧,故将其归为此类。此类以傩戏、撮泰吉、阳戏最具代表性。傩戏,又称“傩堂戏”“傩愿戏”“跳神戏”“师道戏”“脸壳戏”,是一种戴面具表演的祭祀戏剧。傩戏是贵州省内最具代表性的祭祀仪式性戏剧之一。贵州傩戏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早在明嘉靖年间祈求平安的傩戏已在贵州地区十分盛行。贵州傩戏以德江、道真、荔波、岑巩、印江、石阡、织金、江口、湄潭、纳雍、息烽、水城、沿河、思南、册亨等地最为盛行。傩戏由傩祭、傩舞融合民间说唱艺术、戏曲艺术的内容与形式发展而来。贵州傩戏是高度成熟且综合性极高的表演艺术。彝族撮泰吉是贵州最古老的傩戏剧种。“撮泰吉”系彝语,意为“变人戏”。在表演形式上,彝族撮泰吉以黑底白纹面具为饰,以抽气式唱腔为主,以罗圈腿舞姿为特色,与其他唱腔悠扬婉转、舞姿眉目传神的戏剧存在明显差异。阳戏是傩戏的一个子系统,是一种以祈福禳灾为本质的融合民间说唱、表演艺术的祭祀性戏剧。包括贵州阳戏在内的中国西南阳戏源于江南地区,根植于殷商文化[4]。贵州境内有三个阳戏文化带,即黔北的沿河、湄潭、息烽等地的仪式阳戏带;黔中地区福泉、开阳、黔西的仪戏结合性阳戏带;黔东南地区天柱、锦屏、黎平等地民间小戏性质的阳戏带[5]。傀儡戏剧主要有安顺地戏、石阡木偶戏。安顺地戏虽属军傩范畴,但它以蒙青巾戴面具为突出特征,是贵州傀儡戏的典型形态,故将其归为傀儡戏剧。安顺地戏表演多在岁首或七月稻谷扬花时开展,故有“玩新春”和“跳花神”之名。安顺地戏表演一般包括“开财门”“扫开场”“跳神”“扫收场”四个部分。演出时,表演者头蒙青巾,腰围战裙,额前戴假面,手持戈矛刀戟等武器,在一锣一鼓的伴奏下说唱七言、十言韵文,应声而舞,表现征战格斗场景,给人以雄浑粗犷、古朴刚健之感。石阡木偶戏是主要流传于铜仁市石阡县花桥、坪山、汤山一带的杖头木偶戏,是宋元以来杖头木偶戏在贵州民间的遗存。演出时,表演者通过手杖操纵木偶。从唱腔来看,石阡木偶戏以“辰河腔”为主,包括“高腔”和“平弹”两部分,属湘剧范畴。民间小戏主要有花灯戏、马马灯、茶灯等。其中,以花灯戏流行地区最广,以马马灯表演形式最为独特。花灯戏是广泛流传于贵州的一种地方戏剧艺术,以手不离扇(帕)、载歌载舞为突出特征。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贵州花灯戏突破了传统的“灯、扇、帕”歌舞程式和“二小”(一生一旦)、“三小”(一生二旦)角色行当的限制,舞蹈步法繁多,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根据流传地和唱腔,贵州花灯戏可以分为东、南、西、北四路[6]。东路花灯俗称“高台戏”“花灯戏”,主要分布在铜仁、印江、思南、德江、石阡等地,唱腔具有戏曲性较强、高亢开朗的特征。南路花灯俗称“台灯”,分布在独山、福泉、罗甸等地,唱腔具有叙事性强、起伏跳跃幅度大的特征。西路花灯俗称“灯夹戏”,分布在安顺、普定、平坝、黔西、大方、金沙、水城等地,唱腔具有委婉清新、跳跃诙谐的特征。北路花灯也称“灯夹戏”,分布在遵义、湄潭、余庆、赤水、仁怀等地,唱腔具有生活气息浓郁、富于诵唱的特征。马马灯是主要流行于沿河土家族聚居地区的民间小戏,以演员套“马”和“马车”表演而得名。“马”和“马车”以竹篾编织成形再糊上皮纸用笔略加勾勒而成。表演时,演员将“马”或“马车”捆在腰间,搭配碎步、跑跳步、跑马步、四方步等基本步法和板腔体、曲牌体、花调子等唱腔。跳马马灯一般需要12人,分别扮演引路人、乘车人、推车人、骑马人、牵马人的角色。出场时,演员呈丁字形队列,头戴面具、手执马鞭的引路人走在队首;双手执帕的乘车人、腰间套“马”的骑马人走在中间;推车人在车子后头;腰捆红布带,手执大刀或金箍棒的牵马人在马右侧。综观而言,非遗名录中的贵州传统戏剧类型丰富多彩,既有原始古朴的撮泰吉、木偶戏,也有戏剧化水平较高的侗戏、花灯戏;既有仪式性特征鲜明的傩戏,也有娱乐大众、诙谐打趣的阳戏;既有民族特色突出的布依戏、侗戏,也有地域特征鲜明的地戏。入选非遗名录的贵州传统戏剧是贵州传统戏剧的精华,是贵州传统表演艺术的典型代表。贵州传统戏剧的民族性、古朴性、交融性特征在入选非遗名录的贵州传统戏剧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少数民族戏剧是入选非遗名录的贵州传统戏剧的重要类型。苗族、土家族的傩堂戏、布依族的布依戏、侗族的侗戏、彝族的撮泰吉、仡佬族的花灯戏等少数民族戏剧既有中华民族戏曲的共有艺术特征,又具有各民族独特历史发展过程、经济生产方式、宗教信仰、文化生态环境等因素所赋予的鲜明的民族特色。贵州少数民族传统戏剧多用本民族语言、传统唱腔进行演唱,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民族舞蹈元素;在戏剧内容方面,或以本民族民间传说、经典故事为题材进行创作,或在汉族经典曲目中融入本民族的道德观、伦理观、审美观。入选非遗名录的贵州传统戏剧布依戏用布依语演唱,并且基本保留了布依族传统的“八音坐唱”的形式;侗戏用侗语演唱,融入了侗族大歌的元素;彝族撮泰吉则保留了彝族祭祀仪式的原始样态。尽管贵州境内不同民族的傩戏各有特色,但其本质属性是相同的,是多民族共有共享的文化事项。傩戏发源于以歌舞娱神的傩祭,是贵州戏剧文化中最久远、最原始古朴、最具地域特色的代表性剧种之一。古代贵州以歌舞娱神为主要特征的傩祭之风盛行。唐代中原傩习俗与黔域巫风融合,逐渐发展为一种民族性的、地域性的傩俗,为土家族、苗族、侗族、布依族、水族、仡佬族、彝族等多民族共有共享。宋元时期,贵州傩祭由娱神趋向娱人,在傩歌傩舞基础上增加了故事性,初具傩戏雏形[7](P17-19)。贵州传统戏剧基本具备中国戏剧“歌舞演故事”的特征,其“歌舞”多以傩歌傩舞为原型。与现代戏剧艺术相比,傩戏“属于不完整的稚拙的艺术形式”,虽然历经“三千年迟滞的发展”,但是“仍未突破和脱离宗教祭祀仪式的桎梏和羁绊,走上完全世俗化的现代戏剧道路”[8],保留了较强的原始性和古朴性。综观非遗名录中的贵州传统戏剧,在14项国家级(含扩展)项目中,安顺地戏、德江傩堂戏、彝族撮泰吉、仡佬族傩戏、荔波仡佬族傩戏、傩戏(庆坛)6项属傩戏范畴,占比42.86%。在50项省级(含扩展)项目中,思州傩戏傩技、德江傩堂戏、仡佬族傩戏、思州喜傩神、镇远土家族傩戏、印江等地傩戏、湄潭等地傩戏、息烽等地傩戏、安顺地戏、蓬莱布依地戏、马路屯堡地戏、开阳地戏、关岭地戏、花溪地戏、高台地戏、龙场地戏、折溪地戏、金沙端公戏18项属傩戏范畴,占比36%。此外,阳戏也占据重要比例。目前,非遗名录中的贵州传统戏剧有贵阳阳戏1项国家级项目和福泉阳戏、天柱阳戏、沿河等地阳戏、正安阳戏、碧江区等地阳戏5项省级项目,分别占比7.14%和10%。总体而言,傩戏与阳戏在入选非遗名录的贵州传统戏剧中总占比为46%,占总数的近一半。由此可见,傩戏及其子系统是入选非遗名录的贵州传统戏剧的核心组成部分,在贵州戏剧文化系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傩戏是贵州传统戏剧的基底,深刻影响着整个贵州传统戏剧文化系统。因此,以傩戏为基底和核心组成部分的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同样呈现出较强的原生性和古朴性特征。作为中国传统戏剧的组成部分,贵州传统戏剧融贵州独特的民间文学、民族音乐和舞蹈、地方雕刻与绘画、武术与杂技等艺术元素于一体,同样呈现出鲜明融合性特征。这一点在入选非遗名录的贵州传统戏剧中体现得更为突出。诸如,安顺地戏中既有《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五虎平南》《精忠报国》等金戈铁马的征战文学,也有武术套路和刀、枪、剑、戟、鞭、锏、斧、棍、矛、钩、铛等十八般兵器,还有武将、文将、道人、杂扮、动物等假面雕刻艺术,是一种典型的文学、武术、雕塑等方面的艺术融合体。贵州传统戏剧也是不同民族文化交融共生、不同地域文化交流互鉴的产物,融合多民族、多地域艺术元素、戏剧内容、表演形式于一体,呈现出鲜明的交融性特征。贵州传统戏剧的交融性特征在入选非遗名录的贵州传统戏剧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侗戏、布依戏、花灯戏、傩戏、阳戏无一不是民族文化交融共生、地域文化交流互鉴的产物。侗戏系19世纪30年代贵州黎平县村民吴文彩将侗族大歌、琵琶歌与汉族戏剧融合而成,由侗乡人组成剧团,身着侗族服装,用侗族方言演唱。侗戏剧目主要取材于侗族和汉族的民间传说,还有部分侗族剧目直接改编、移植于汉族戏曲剧目,借用汉戏剧目情节,但基本结构、形式按侗戏特质编写,如《陈世美》《梁祝姻缘》《生死牌》《十五贯》等。布依戏是典型的多民族文化交融的产物。在戏剧音乐上,布依戏以布依族传统的“摩公调”为基础,借鉴广西彩调、贵州花灯戏,创造“灯调”和“喊板”唱腔,并融合布依族八音坐唱的唱法和节奏。贵州花灯戏是明清时期随着徽赣、苏浙、两湖、川陕等地汉族移民入黔传播而来的采茶、花鼓一类的农田表演艺术[7]。花灯戏传入贵州之后,在调子、调式上融入了许多民族风格和地方元素,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四种类型。傩戏是在傩歌傩舞的基础上融合民间说唱、戏曲内容与形式发展而来的“歌舞演故事”的表演艺术。贵州傩戏种类繁多,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傩戏之间在剧目、表演形式等方面各有借鉴。诸如:侗族傩戏表演时,在侗族民歌基础上部分吸收花灯戏和阳戏唱腔,在民族舞蹈基础上吸收了一些汉族身段;贵州省道真自治县仡佬族傩戏在传承仡佬族民族信仰文化的同时,将汉族戏剧故事情节进行改编后融入本民族传统文化之中。阳戏是傩戏的子系统,相比傩戏,有更强的包容性和更鲜明的交融性。贵州阳戏发源于江南地区,途经四川、重庆、江西等地传入黔境,在传播过程中融合了川渝赣等地的傩戏、弋阳腔、采茶调等民间娱乐形式,扎根黔北、黔中、黔东南等地后又融入了地方民间故事、民间歌舞以及花灯、花鼓等地方曲艺形式,强化了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更具世俗性和娱乐性。三、非遗名录中贵州传统戏剧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的文化积淀,蕴含着深厚的家国情怀以及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追求,承载着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良好品质和自信自强的精神根基,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精神支撑、价值支撑和历史文化资源。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贵州传统戏剧的精华,非遗名录中的贵州传统戏剧在增强贵州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增强贵州各民族对本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民族认同是一种民族意识,以共同的文化符号体系为基础,具有情感的归属价值。”[9]非遗名录中的贵州传统戏剧在增强民族认同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增强贵州各民族对本民族的认同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两个方面。一方面,部分非遗名录中的贵州传统戏剧,尤其是少数民族戏剧是单一民族独特的文化符号体系,在增强民族内部凝聚力和归属感、强化对本民族的认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部分非遗名录中的贵州传统戏剧,诸如傩戏是多个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历史经验,有助于增强贵州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以侗戏为例。侗戏是入选非遗名录的贵州传统戏剧的代表项目,在增强民族认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侗戏是在侗族大歌、侗族民间说唱艺术的基础上综合汉族戏剧元素发展而来,既具有浓厚的侗族文化特色,又承载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历史事实。作为侗族文化的核心符号之一,侗族民众可通过侗戏强化对本民族的认同。通过侗戏表演,侗族与汉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图景得以呈现,中华民族一家亲的观念深入人心,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得以强化。戏剧在强化中华文化认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贵州传统戏剧的典型,入选非遗名录的贵州传统戏剧呈现出的文化共性和认同意识更为突出,可“让各民族共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让非遗成为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10],进而强化各民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认同。第一,强化贵州各民族对儒释道文化的认同。中华信仰体系以儒释道信仰为主导和主体。儒释道“三者的互融互补共同奠定并塑造了汉族的文化心理结构”[11]。在入选非遗名录的贵州传统戏剧中,以传奇故事为题材以及宣扬忠孝节义、三纲五常、诚信修睦、尊师重教等思想的剧目比比皆是,象征公正、忠诚、威武、刚烈、慈祥等人物性格的面具也不乏其数。通过戏剧这种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演形式,儒释道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被贵州各民族所认同和吸收。第二,强化贵州各民族对崇宗敬祖文化的认同。崇宗敬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家族观念与祭祖行为一直是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共有共享的价值取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情怀。在入选非遗名录的贵州传统戏剧,尤其是傩戏中,不乏对崇宗敬祖观念和行为的艺术性表达。诸如,彝族撮泰吉仪式之初布摩手持泡木树棍向天地、祖先、四方神灵祈祷,正是他们崇宗敬祖观念的行为表达。因此一定程度上可将撮泰吉视为彝族祖先崇拜的祭祀仪式展演。又如,德江傩戏表演前要先安坛并禀告主家家先,表演时要向家先献祭,表演结束后要重新安置家先。这是土家族人祖先崇拜的艺术表达。通过戏剧文化交融,汉族基于家族本位的祖先崇拜观念与贵州少数民族原始古朴的祖先崇拜观念得以交流互鉴,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崇宗敬祖文化。同时,通过戏剧表演,中华民族崇宗敬祖文化得以在贵州民族地区广泛传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贵州各族人民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第三,强化贵州各民族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认同。弘扬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戏剧对弘扬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强化各民族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认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中国传统戏剧以丰富多彩的表演形式演绎家国情怀、个人爱恨情仇,传播忠孝节义、是非善恶等价值观念,“与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终极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2]高度契合。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戏剧寓教于乐的艺术追求不仅能够体现时代精神,还能够以丰富多彩的表演形式和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模仿人物行为,再现事物状态,正面或反面反映出人们行为准则和价值评判,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观众的思想观念和言行举止。贵州传统戏剧以爱国爱家、忠孝节义、婚恋自由等为主题,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内在统一性。地戏、侗戏等倡导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契合。安顺地戏“每一部都以朝廷作为情节的起点和终点,让故事中的英雄们受委派从朝廷出发,经过征战讨伐,最终取得胜利,又回到朝廷报功复命”[13],反映了屯堡人以正统国家武士身份自居、忠于朝廷的价值观念,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今社会倡导的家国情怀。侗戏主要以“反抗权贵”和“爱情忠贞”为主题,戏剧情节突出善恶对立、爱恨情仇,宣扬惩恶扬善、爱情忠贞,提倡自由、平等,劝导友善待人、勤劳勇敢、和睦邻里、尊老爱幼。通过对贵州传统戏剧的保护和活态传承,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无疑有助于强化贵州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14]是时代之需,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重要途径,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必然要求。从根源上推动贵州传统戏剧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创新,能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征途上大放异彩并贡献出其应有的精神力量,这对于促进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均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15]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名录中的贵州传统戏剧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索和研究。
参考文献:
[1]周灵颖.传统戏剧类“非遗”群体传承研究——以昆明民间花灯剧团为例[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
[2]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项目目录[EB/OL].(2023-05-28)[2024-07-21].http://www.gzfwz.org.cn/gjml.
[3]何琼.贵州少数民族传统戏剧文化及当代转换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4]吴电雷.论西南地区阳戏之“源”与“流”[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2,(11).
[5]吴电雷.论黔域阳戏形态及其文化渊源[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
[6]扶燕,龙国洪.贵州花灯戏唱腔的形成及其风格[J].中国戏剧,2013,(4).
[7]王恒富.贵州戏剧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
[8]曲六乙.守望少数民族戏剧精神家园确立中华民族戏剧史观——《中国少数民族戏剧通史》前言[J].戏曲研究,2012,(2).
[9]吴建冰.论侗族戏剧中的民族认同[J].戏剧文学,2017,(3).
[10]杨玉兰,段超.贵州加快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建设的路径[J].贵州民族研究,2023,(6).
[11]刘敏.艺术交融与中华文化认同的视觉表达——以白族民居彩绘艺术为例[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
[12]王冠平.中国传统戏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D].西安:西安工业大学,2017.
[13]朱伟华.建构与生成——屯堡文化及地戏形态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4]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2).
[15]潘光繁.传承与创新:数字人文促进水族古歌的研究与应用[J].贵州民族研究,2023,(3).